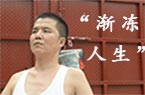8月26日,山西晉中榆次——河北張家口。途經雁門關,行車9小時10分鐘,行程556公裡。
之前,25日在山西晉中榆次採訪行程58公裡。
目前,總行程2526公裡。
當年,茶商們趕著牲口拉著車,從山西出發,有兩條路:一條過雁門關到張家口,稱“走東口”﹔一條出殺虎口到呼和浩特,稱“走西口”。
如今,我們選擇“走東口”,上二廣高速,轉張石高速到張家口,一天內抵達。所行路線與當年大致重合。
行程
名家茶話
一個口,三種城
特派記者李皖 發自河北張家口
張家口的陽光是白亮的,天空碧藍,高空的風把雲拉成細條狀,下面長城開了一個口子,城門上書“大好河山”。
明顯感覺是到了北地了:光線、氣候、風土裡有一種微妙細節,透著說不出的不一樣。陽光下干熱,陰影中透涼,此地人嗜茶,與前一站晉中,一下子拉開好大距離。
我們的“名家茶話”被安排在桂府茶樓,一個滿樓是茶、茶風扑面的地方﹔交談對象是劉振瑛,張家口地方史專家,本地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
記者:劉老師,剛才你在路上說的,“一道長城,小大兩門﹔一條商道,下上二堡﹔一條鐵路,西東兩區”,對張家口的概括真是非常精彩,能不能再解讀一番?
劉振瑛:張家口先有小境門再有大境門,先有下堡再有上堡,先有西區再有東區,發生順序是反著的,非常巧合。而塑造這座城市的東西,先是長城,再是商道,最后是鐵路。伴隨著這三樣,形成小大境門、下上二堡、西東兩區三種城市格局﹔三種城市格局,產生於明、清、現代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記者:不管哪種格局、哪個階段,這個城市的核心是一個“口”字。
劉振瑛:不錯。張家口三面環山一面留口,明代用長城把這個口封起來,成為軍事要塞。清代把這個口打開,開放互市,成了陸路商埠。近代第一條鐵路從北京修到張家口,新區東區又爆發了。
記者:從東區到西區,過一條河,突然就從一個現代化的都市進入一個古代的老城,很令人意外。
劉振瑛:張家口的造城史是分片的,每一片時空各自獨立,不交雜。
記者:我注意到這裡的人很“交雜”。在街頭,你看每個人的臉,很多樣。廟裡供的神,也多樣,不同教的神混居一處。
劉振瑛:張家口是座移民城市。每個人都說自己是張家口人,但其實所屬人種不一樣。尤其是清代,南北東西各民族、中蒙俄人,都到口子來互市,人口由1萬爆發到十幾萬。北方市馬,南方運茶,南來北往,駱駝牛馬人,很熱鬧。
記者:它一直就是這樣的集市。萬裡茶道讓它的規模一下子膨脹了,是這樣吧?
劉振瑛:是這樣,這是它最非凡的時期,因此國際聞名,打上了俄蒙印記。蒙古人把這個地方叫“門”,變成蒙語就是“卡拉根”。俄羅斯人也便把它叫“卡拉根”。有一年俄羅斯代表團來,問市長“卡拉根”在哪裡。現在加拿大航班,也還是把這裡叫“卡拉根”。
記者:它可真是一個多民族大融合的門,萬裡茶道的北方大門。
張家口大境門
張家口堡子裡老城,街巷內仍住有很多居民,以老人居多
中俄茶葉貿易,帶動了萬裡茶道沿線一批城市的發展與繁榮,因“張庫大道”而興的河北張家口市,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張家口西北東三面環山,一條河流貫穿南北。周圍的山勢南寬北窄,到北部有一山口“大境門”,出了山口,就是通往蒙古高原的狹長孔道,一直通向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被稱為“張庫大道”。“張庫大道”是當年茶葉貿易重要的運銷線路,興於1860年前后。經張家口到塞外的這一條商業之路,也就是人們俗稱的 “走東口”。
8月27日,本報“重走中俄萬裡茶道”採訪團來到張家口市,探訪古城茶市、大境門等地,試圖尋找當年中俄茶葉貿易留下的蛛絲馬跡。
堡子裡擁有眾多茶商總部
採訪團來到張家口的第一站,是被當地人稱為“堡子裡”的老城。堡子裡是“張家口堡”的俗稱,明朝時期防止蒙古軍隊進犯的軍事要塞。
如今的堡子裡,主街是一條復古商業街,距離市中心不遠。張家口地方史專家劉振瑛介紹,明清時期,隨著張庫大道茶葉之路的日漸興盛,張家口堡的商業貿易功能越來越強,最后將其軍事功能覆蓋。
“當時,‘堡子裡’山西商人很多”,劉振瑛說,這裡有當時全國最負盛名的票號“日升昌”,中外茶商雲集此處,鼎盛時期堡內票號、商號達1600多家。晉商大戶常家就是發家於此,在此設有大德玉、大涌玉等茶庄總號。
記者探訪看到,堡子裡隨處可見山西風格的單檐屋舍。老街上,常家創始人常萬達興建的大美玉商號,仍是街巷中的最高建筑,門口還留有當年的龍頭雕飾。
劉振瑛說,清代時期,張家口有四大茶庄:大裕川、大玉川、長裕川和長盛川。以大裕川茶庄為例,當年,清廷曾為其經營的茶葉賜予紅色“雙龍票”,使其購銷暢行無阻。清乾隆帝賜予茶庄“雙龍石碑”,上面鐫刻著大裕茶庄對發展中俄、漢蒙貿易的貢獻。“常家門口的龍頭,應該就是獲贈於此”。
大境門外的“旱碼頭”
張家口三面環山,獨特的地理環境使之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距離張家口市中心4公裡左右的大境門,當年是山口處扼守張庫大道的咽喉,被稱為“中國萬裡長城四大關口之一”。
劉振瑛介紹,大境門修筑於清順治元年(1644年)。“修筑大境門,是清政府對張庫大道這條商業運輸線的極大支持。”他說,當時,張家口出大境門向西,近十裡的狹長溝谷中,寸土寸金,商號店鋪鱗次櫛比,交易市場人聲鼎沸。
“外商也紛紛來此”,劉振瑛說,據記載,當時設在張家口的外國商行有英國的“德隆”、“仁記”、“商業”、“平和”,有德國的“禮和”、“地亞士”,有美國的“茂盛”、“德泰”,有日本的“三井”、“三菱”,還有法、俄、荷蘭等的商行,總數達44家,可以和同一時期的天津、上海相媲美。
記者看到,目前大境門與周圍長城部分正在修繕,以開發旅游。劉振瑛所說的“十裡溝谷”,目前正在興建新的復古商業街,大多面目全非。隻有西側小境門內一條深深的車轍印,依稀可見清代詩人描述的“車轍行騰市井囂,百年休養得今朝,黃雲匝地遮沙漠,衰草連岡走駱駝”的景象。
《茶葉之路》一書作者鄧九剛說,張庫大道的繁盛,與漢口開埠密不可分。1861年,清政府與中、法、俄簽訂《北京條約》,漢口成為新辟的通商口岸。1862年,俄國與清政府簽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使俄商們取得在中國南方直接在茶區採購加工茶葉的權利﹔且俄商在中國邊界百裡內免稅。“張家口成為俄商觸角伸往中國內地的必經之地”。
張家口因“走西口”隱而不張
8月25日,採訪團在山西晉中榆次走訪獲得新史料。
據榆次區史志辦劉錦萍研究分析,清政府南下入主中原前,因晉商一直在北方進行邊境貿易的緣故,清與晉商之間有一種“近親”的情感。為“財賦有出,國用不匱”,清政府需要晉商為他們購買、輸送各種物資,以穩固邊塞,於是冊封了盤踞張家口從事邊疆貿易的八家晉商為皇商。
華商赴恰克圖進行中俄貿易,須獲得清政府的信票(即龍票),無票不准入市。信票隻有張家口(清政府察哈爾都統張家口衙門)才有權發放,一年辦兩次,以舊換新,其他地方政府一律無權。“這就使晉商壟斷了全部的恰克圖貿易”,劉錦萍說。
“山西榆次曾經的晉商時代,都是‘走東口’的商人,包括茶葉之路上排名第一位的常家和排名第二位的郝家,民間人丁的十之三四依附而行,何等壯觀。”
而“走西口”之路,是萬裡茶道上的旁支。這條從殺虎口到呼和浩特的路,是山西也包括其他北方商人,假道旅蒙走私俄國的販茶之路。
“走西口”走私茶葉的性質,在清咸豐年間改變,一個叫程化鵬的山西商人,代表西口商戶請願,使清政府信票發放權擴大到了呼和浩特。由此,“走西口”的私商由暗轉明,堂堂正正融入到茶葉之路浩浩蕩蕩的對俄貿易大軍中。“這段歷史記載在《山西獻征》程化鵬事略中”,劉錦萍說。
8月27日,張家口堡子裡老城鐘樓
本版圖片 特派記者 胡冬冬 攝
在張家口拜謁俄商無名墓 附近曾是萬裡茶道“旱碼頭”
本報河北張家口專稿 特派記者萬建輝
8月27日,在張家口元寶山半山腰,本報“重走萬裡茶道”採訪團找到了遺留在這裡的近代俄國商人墓地,通過走訪當地村民,初步揭開了這塊墓地背后的故事。
破碎墓碑殘存俄文
進大境門往西溝,一條公路沿著大沙河河床向北延伸。
隨行的《張家口日報》記者手指河溝西面、元寶山半山坡上說,那就是俄商墓。
記者和幾名團隊成員爬上土坡,眼前出現大U字形石牆圍出的一片平地,步行測量,長約40米,寬約30米,地上可見10個土坑。
幾株矮樹下有石塊。走近看,是破碎的墓碑。石條和幾塊石塊上看得見俄文,隻留下上半截,下半截字母已斷掉不見。通過兩個條形石塊長度,可推斷出墓碑平面為長方形,約長1.8米,半人高。
在墓地面向公路的方向,有當地政府於2011年立的碑,碑上有“俄商墓遺址”5個紅色大字。背面刻文:“俄商墓元寶山村西側南山腰處,墓地主人在山腰修筑了三個平台並修建了護坡,墓地位於最上面一個平台……張庫大道興盛時期,俄國商人在此經商,入鄉隨俗,死后就地埋葬。據當地人介紹,其后人已於20世紀80年代將骨灰遷走,現在,基址還依稀可見。”
多國洋行入駐“旱碼頭”
碑文所述,與張家口地方史專家劉振瑛告訴我們的情況基本一致。但俄羅斯墓碑是什麼時候立的?葬了多少俄國商人?墓碑為什麼會被破壞?這些問題仍不明了,劉振瑛和本地隨行記者也不清楚。
劉振瑛証實,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后,從漢口到俄羅斯恰克圖的“茶葉之路”要經過張家口,張家口成為中俄貿易的重要陸路口岸。當時清政府海關收入的兩個主要來源,其中之一就是張家口的關稅。
1909年,京張鐵路開通,張家口的中俄貿易達到頂峰。張家口成為馳名中外的“陸路商埠”,被冠以“旱碼頭”美名。
當時大沙河河谷的元寶山、石匠窯、南天門一帶,俄國茶庄、洋行、郵局、銀行林立,英、美、日、法、德的洋行也來到了這裡。
特派記者鄭汝可 李皖 發自河北張家口
(來源:長江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