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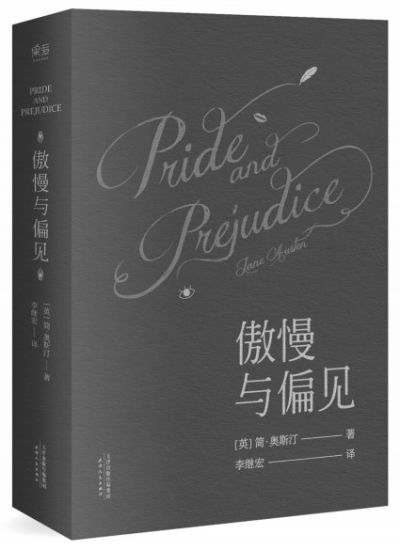
《傲慢與偏見》
作者:【英】簡·奧斯汀
譯者:李繼宏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青年譯者李繼宏因翻譯胡賽尼的《追風箏的人》而知名,同時他也因經常給前輩翻譯家的譯本挑錯而受到爭議。近日,李繼宏歷時三年翻譯的《傲慢與偏見》出版,他為簡·奧斯汀的名著寫了近200頁的注釋。李繼宏接受京華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這些年對於翻譯會更苛刻,他覺得最難翻譯的是《魯濱遜漂流記》。
翻譯《傲慢與偏見》的過程?
大量查閱作者創作背景
2011年夏天,出版人路金波找到李繼宏,問他翻譯20種歐美文學名著需要多長時間?那時李繼宏已經翻譯出版了16種著作,包括《追風箏的人》《維納斯的誕生》《公共人的衰落》《燦爛驕陽》等,有不少是利用業余時間完成的,當時年輕氣盛的他回答:“三年。”
如今,5年過去了,李繼宏翻譯了《了不起的蓋茨比》《老人與海》《小王子》《動物農場》《月亮和六便士》《瓦爾登湖》,加上這次的《傲慢與偏見》一共7部。怎麼越翻譯越慢?李繼宏說:“一開始還比較順利,前四種在2013年年初就完稿了,到了《瓦爾登湖》一下卡住了。之前像《追風箏的人》大多是當代作家寫的書,翻譯起來沒什麼障礙,但是世界名著不是這樣,需要去了解那個時代的背景。”為了翻譯《瓦爾登湖》,他花費了4000多個小時來查閱資料,去弄清梭羅著作中所引用的東西方經典,以及新英格蘭地區動植物的名字。
這次翻譯《傲慢與偏見》又遇到了不小障礙,李繼宏透露,第一頁的半個句子就把他難住了。“He came down on Monday in a chaiseand four to see theplace.”為了弄清這個句子的意思,他三個月沒有動筆。“簡·奧斯汀在18世紀末創作的,那時候的衣食住行、道德觀念、法律制度、社會風氣等等和現在的英國大不相同,如果對那段時期的英國歷史缺乏足夠的了解,根本談不上准確翻譯。”
李繼宏透露,為了了解簡·奧斯汀生活的社會背景,他甚至查閱了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上半葉近百年的英國法律條文。在他撰寫的近200頁注釋說明中,有大量是關於那個時期英國的衣食住行,以及社會風俗的。
這版的《傲慢與偏見》剛剛上市,還看不到太多讀者對李繼宏譯本的反饋。在知乎網上,有網友說:“名著翻譯原本就跟譯者的個人風格、習慣息息相關,從來不應該一枝獨秀,只是百家爭鳴而已。”還有網友稱,李繼宏的有些注釋是“想太多了”,“這麼多的文獻工具就是給我們用的。但是查了些不充分的資料,做了些不靠譜的推斷,就認定自己看出了微言大義,把前人的工作都視為垃圾。”
如何看待翻譯這件事?
有時譯者就像一個演員
李繼宏現在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研究員,被問及日常的工作狀態,他說平常自己沒什麼社交活動,除了偶爾出去旅游,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他舉了一個例子,當初翻譯《瓦爾登湖》時,為了弄清梭羅的閱讀史,他特意到了一個博物館,裡面有340多種梭羅看過的書籍,他一本一本地翻閱了一遍。
談到這幾年心態上有什麼變化,李繼宏說:“我現在准備把原來翻譯的一些書修訂一下,比如我重新看原來翻譯的《維納斯的誕生》,裡面找出來一大堆錯誤。我覺得一開始翻譯就像小孩學畫畫,當慢慢地成長為一個畫家時,對於自己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了,也很難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了。我現在也是類似的狀態,有時候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中國很多老一輩的翻譯家,一直隻專注翻譯一個外國作家的作品,而李繼宏這些年翻譯的著作卻沒什麼規律。對此,他說:“我覺得,有時譯者就像一個演員,要在不同的劇作中演好不同的角色。有的演員一生隻喜歡塑造一種人物,而我喜歡不同的嘗試,喜歡進入不同的情境,去表演不同的人物。”
《追風箏的人》為何受歡迎?
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
當初翻譯《追風箏的人》時,李繼宏還是中文出版方世紀文景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員。這是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賽尼2003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故事講述了一個富家少年與家中仆人關於風箏的故事,關於人性的背叛與救贖。
近幾年,這本書一直佔據國內各大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列,為何這麼受國人歡迎?李繼宏說:“這確實值得思考,其實這本書剛出來的時候在美國也就前幾年賣得好,現在在美國亞馬遜的排名在3000名左右。有人說,在國內賣得好是因為高圓圓的推薦,有一定道理,但在她推薦之前已經賣了300多萬冊了。我覺得一方面是這個故事符合中國人的一些想法和閱讀習慣,再就是閱讀體驗比較好,行文比較流暢。有時候,一本書出來是有它自己命運的。”
在採訪中,李繼宏透露,當初中文出版方簽《追風箏的人》的版權時隻花費了1500美元,這本書的收益是很大的,而作為譯者並沒有獲益太多,“最近又續簽了這本書的翻譯版權,這次給了15萬元”。這其實也是國內譯者面臨的一個困境,翻譯稿費本來就低,有些出版社還要求書正式出版后再結稿費。這次與路金波簽約,李繼宏是按翻譯著作的實際銷量拿版稅的。
□鏈接
《傲慢與偏見》的譯本開頭對比
李繼宏版
有個道理眾所周知:家財萬貫的單身男子,肯定是需要一位太太的。
這樣的道理極度深入人心,所以每當這樣的單身男子喬遷新居,鄰居們哪怕對其思想感情一無所知,也會把他當作自家這個或那個女兒贏得的財產。
“親愛的本尼特先生,”他夫人那天對他說,“你聽說了嗎?內德菲爾庄園終於租出去啦。”
本尼特先生說尚未有所耳聞。
“但已經租掉了,”她回答說,“羅恩太太剛才來過,是她說給我聽的。”
本尼特先生沒有回答。
“你不想知道是誰租的嗎?”他妻子急不可耐地問。
“你要是想說,那我聽聽也無妨。”
本尼特太太立刻抓住這個機會。
“哎呀,親愛的,你一定知道,羅恩太太說,內德菲爾庄園的租客是個特別有錢的年輕人,英格蘭北方來的﹔他禮拜一坐著一輛四驅翠軾從倫敦來看房子,看了以后十分喜歡,當場同意莫裡斯先生提的條件﹔他將會在米迦勒節之前接管這座房子,佣人們下個周末就先搬進去。”
王科一版
凡是有錢的單身漢,總想娶位太太,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
這樣的單身漢,每逢新搬到一個地方,四鄰八舍雖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見解如何,可是,既然這樣的一條真理早已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們總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個女兒理所應得的一筆財產。
有一天班納特太太對她的丈夫說:“我的好老爺,尼日斐花園終於租出去了,你聽說過沒有?”
班納特先生回答道,他沒有聽說過。
“的確租出去了,”她說,“郎格太太剛剛上這兒來過,她把這件事的底細,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
班納特先生沒有理睬她。
“你難道不想知道是誰租去的嗎?”太太不耐煩地嚷起來了。
“既是你要說給我聽,我聽聽也無妨。”
這句話足夠鼓勵她講下去了。
“哦!親愛的,你得知道,郎格太太說,租尼日斐花園的是個闊少爺,他是英格蘭北部的人﹔聽說他星期一那天,乘著一輛駟馬大轎車來看房子,看得非常中意,當場就和莫理斯先生談妥了﹔他要在‘米迦勒節’以前搬進來,打算下個周末先叫幾個佣人來住。”
京華時報記者 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