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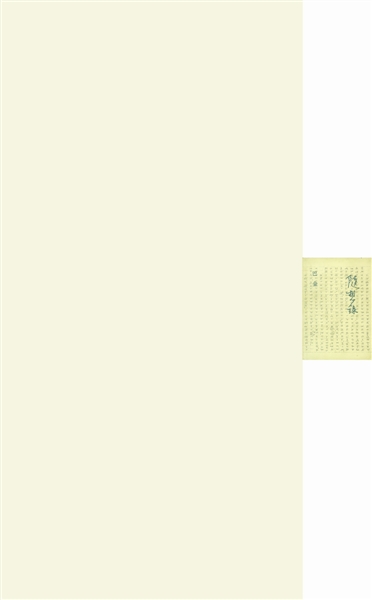
◎李 辉
编者按:今天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物质狂欢的时代,让我们回到一种节制的安静中,或许能听到巴金先生在对我们说什么。记住巴金,就是记住一个时代。
一
一个伟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时代的产儿,也是他所属时代的代表。
巴金走过漫长的百年历程,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一九〇四年出生的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获得思想、精神与文学的滋养、力量,走过风雨,在起伏跌宕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二〇〇五年,最终与他经历的时代永远告别。
岁月沧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经历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世纪……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引吭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他的时代。
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把心交给读者。”
“讲真话。”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尽全力这样在做。
如今,迎来巴金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人们追思他,纪念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从《家》《春》《秋》到《随想录》,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响过他的读者和他的时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珍爱和传承他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文学遗产。
历史,永远是一种延续。
回顾、思考与传承,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纪念。
二
近年来,人们常常以不同方式回忆八十年代,谈论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只是一个时间的起始,我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接下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看作八十年代的先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
恢复高考是教育的理性回归,是告别混乱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将之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范围,即可看出,它的最具时代转折的意义,应该是社会终于回到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当年参加高考并有幸录入的不少年轻人,曾多年背负着父辈的“原罪”包袱,其中,通常所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青少年),比例较大。帷幕既然拉开,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便一一亮相了。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四百四十多万地主、富农摘掉帽子,几十万名右派分子和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相继获得平反……从此,他们的子女,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享有与同辈人一样的平等身份和权利。
改变历史的第一步,已经迈开。这无疑是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一次大变动。多少人的命运为之改变,多少个家庭为之团圆。如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词语之一是“弱势群体”,三十年前,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那些步履蹒跚的归来者,正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贱民”,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期盼与其他群体一样轻松呼吸,期盼自己也能够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周围不再有人投来鄙视甚或仇视的目光,他们的后代也不再背负父辈沉重的政治包袱,可以与别的孩子们一样,伸出臂膀,拥抱阳光,唱一曲自己的歌。
一个国家,不再有阶层划分的整体歧视,才能有凝聚力,才能有活力。
历史的大变动。三十几年已然过去,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当年的这种具体情形,才会对巴金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有较为贴切的理解,也才能对他的《随想录》,以及当年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
三
回想当年情景,晚年巴金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面旗帜。自一九七八年年底开始,他埋头于写作《随想录》,不少文章的发表,总是敏感地呼应着现实问题,在呼应现实的同时,历史的反思增加着思想和精神的分量。
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也是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集体归来之际。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历史反思,无疑成为他写作时始终萦绕于心的主题。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巴金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近年来,重新出现的红卫兵忏悔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与巴金当年的衔接。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一九八〇年四月,巴金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与此同时,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忏悔意识、站在全人类的范畴认识“文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也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原则,一些年里,却在自己身上消灭,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深刻性。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巴金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真诚依然重要,“说真话”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话题。
四
回望八十年代,巴金不只是以《随想录》影响着中国,他还如同三十、四十年代一样,借《收获》的平台,靠自己在文坛德高望重的身份,培养和推出一个又一个后辈作家,让新时期文学的天空,更加宽阔而耀眼。
人们谈到巴金,时常只局限于他的文学创作,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一九五七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直到二〇〇五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十几年间,出版一百多种作品,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汪曾祺、黄裳、黄宗江……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巴金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唯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从维熙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一直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这些年,从我熟悉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冯骥才、沙叶新、张辛欣等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受惠于巴金的那些作家们来说,巴金无疑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五
早在三十几岁时,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表述所感受的生命运动: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九年前,一百零一岁的巴金离开了我们。遵照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与妻子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入东海。
从此,一个人的生命,如激流一般汇入大海。从此,一个矛盾、痛苦,同时又是丰富、伟大的生命,走进了历史。巴金为我们留下温暖而美好的记忆;巴金为我们留下了《家》、《春》、《秋》,留下了《寒夜》,留下了《随想录》;巴金也为未来提供了说不尽的政治的、文化的话题……
巴金的时代已成过去,他为自己的时代发出的声音,却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发出回响。
记住一个人,也就记住了一个时代。
哪怕他已远行。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