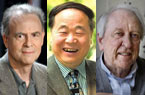2014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巨制。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陈思和
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的第三期(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看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的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的许多相关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乎身处的环境。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基本上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写每卷的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以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爸爸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记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样宽广。
我还想说一件难以启口的事情,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心痛。巴金先生在《全集》第二十卷的跋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树基:
《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
《明亮的星星》等五篇给丢失了。《春天的来信》的改定稿也丢失了,不过江南的原信还登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这个集子的《后记》是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写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子编好托济生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想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待到十年梦醒,手稿回到身边,一放就是几年,我连翻看它们的兴趣也没有。后来编印《全集》,找出旧稿拿去复印,终于丢失,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惜,倒觉得心上一块石头给搬开了。欠债的感觉少一些,心里也轻松些……
这里所说的《炸不断的桥》中五篇稿子“复印终于丢失”,是我造成的严重事故。当时巴金先生在编全集的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几卷,我和李存光分头帮他搜集和影印相关文献。一天巴金先生把两部旧稿交给我,一部是中篇小说《三同志》,是以朝鲜战争为题材,另一部就是散文集《炸不断的桥》,以越南战争为题材,都是手稿,交给我去复印,准备编入全集。
我拿到稿子,马上去学校复印了。但正是这个时候我在搬家,忙着整理东西,我怕一些珍贵东西丢失,就特意把这两部手稿连同复印件,还有一些其他待印的旧刊物、旧稿,还有我导师贾植芳先生准备整理回忆录的文献资料,这是我所有家当中最最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袋子里,专门放开来。结果真“仿佛命中注定”,等搬完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偏偏这个最重要的袋子找不到了。当时我的绝望和沮丧是他人难以想象的。记得那天我在荒芜的马路边仓皇奔走,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仿佛要压下来似的,真是欲哭无泪。我无法面对我人生道路上最最重要的两位老人,也无法弥补那些丢失的文献资料和手稿。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影印了《三同志》以后,把复印件放在身边阅读,总算没有丢失。《炸不断的桥》里的散文作品,有六篇曾经发表过,剩下的四篇散文和一篇后记,由于我的失误,永远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这个事情。无奈中我找了陆谷苇先生,与他商量。谷苇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携过我的师长,他也是长期关注和报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记者,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报道。谷苇先生竭力安慰我,鼓励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请小林寻机会转告巴老,认为这样比较稳妥。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就去找了小林,难以启齿的事情终于向小林吐露了。我在这里真心赞美巴金先生树立的良好家风,小林听了我的陈述以后一句责备话都没有,反而要我安心,让我写一封信把情况说明一下,由她交给巴金先生。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来,要我去家里。我知道巴金先生已经原谅我了,但还是毫无自信地走进了武康路113号。那天小林和李济生先生都在场,巴金先生坐在沙发上,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不要紧。”接着,老人用安慰的口气说,他有日记,记下了《炸不断的桥》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来。一场对我来说是天大的灾难,也是心灵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伤口,就这样被老人轻轻地抚平了。
这个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伤,但老人的高风亮节,对我做人态度的教育是极大的提升。我从此养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做事习惯,努力克服内心的骄傲以及自以为是的恶习。尤其是与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两位老人有关的工作,我的确是容不得再发生一丝一毫的差错。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轻人常会抱怨,以为我做事过于较真,对没有事必躬亲的事情总是不顺眼、不放心。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即使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难以报答老人的知遇之恩。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