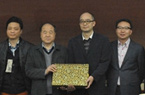文学的铀质在生活深处,文学的魂魄在人民之中,并由此决定了任何文学创作,都既是对人民生活的艺术化反映,又是对大众感情的聚焦式凝结。各种内容与形式的文艺作品,从根本上说,都是驭笔于事和动情于衷的精神产物,所以决不能矫揉造作,更不能“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读玉洁的长篇小说《狗来儿》,首先感到的,是它对深切生活体验的生动描述和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通篇都体现着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厚爱。其次,是它在文学架构和艺术布局上的传承与创新。
《狗来儿》以最朴素的形式诉诸于世的,是最真实的生活和最真挚的感情。其优势在于不渲染、不矫饰、不做作,按照生活的固有逻辑和人们的心路历程与情感轨迹,艺术地还原了客观世界所存在着的心理纠葛和爱恨情仇。而且,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生活的艺术还原上,而是及时地秉持着真、善、美的人性准则,富于张力地对爱恨情仇施以精神裁量与道德评价,并通过合理的艺术回旋,使爱恨情仇实现了具有道德理性的转移与切换,将人性的诡谲有声有色地升格为人性的纯净。
显然,承载和传达这认识价值和精神寓意的,正是《狗来儿》的人物、情节、意境与题旨。作者在50余万字的篇幅中,精心建构了一个现实生活的演示台与世俗社会的横剖面。此中,各色人等的表演虽都具有特色,但又无一例外地代表了一种社会人性的构成与现实生活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各自都既是原型,又是典型。读者从他们身上,每每都能体悟到人的普遍属性和社会的伦常演绎。比如主人公狗来儿,他的勤谨、包容、深厚、善良,就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美德的所有构成要素。而在杨海棠、杨文清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却显然是对这种美德的挑衅与悖逆,狡黠、自私的秉性和诈赖的行为中所潜在着的,无疑都是需要予以谴责和鞭挞的精神孽根与道德沉渣。
作者在作品中所设置的这种基本人物关系以及由之所构成的思想情境与艺术格致,其本身就已形成并确证了出现对立和发生冲突的生活质点与人性本能。而事实上作者也正是利用这种对立和冲突,才得以一浪撵着一浪地把情节推向了高潮,并在矛盾对立不断激化的终点上,出人意料地呈现异乎寻常的破解与转圜,从而实现“理”的回归与“善”的折返。
诚然,这是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上的机巧,但更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层次开掘。任何成功的和有价值、有意义、有效能的文学创作与艺术创造,都只有臻于这样的境界和实现这样的旨归,才能算是对生活真理和文学真谛的准确理解与有效践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狗来儿》不但实现了情节的推进、情感的升华,而且创造了一种以真情代替矫情、用真实置换虚假的艺术风格。
当然,在《狗来儿》所带给我们的新风尚与新气象中,除了纯真、质朴、清新、刚健和情节有致、内容充实、题旨宏阔之外,更有那娴稔的民族化的叙事方式和亲切的乡土化的语言风格。从浓馥的泥土气息和飘逸的民族风韵中所沁渗出来的,不仅是一阵阵田野的清香和一缕缕阳光的映照,更是作者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载和对时代使命的勇敢担当。而这一切所体现和所承载的,则正是对人民性与社会性的深刻发掘与高度浓缩。
由此可见,《狗来儿》的生活化叙事和社会化表意及其对主题、情节、人物、场景的撷获与熔铸,都无不钤刻着时代变革、社会转型的鲜明印迹。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实现路径就是心向人民大众,投身生活洪流。作者玉洁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基层,有着浓烈的乡土情结和深切的生活体验。因此,在这洋洋50余万言的叙说中,处处都凸显真心,流露真情,表达着挚爱生活与人民的拳拳之意。而这,既是《狗来儿》的成功之因和创新之源,又是《狗来儿》的精神“质”点与艺术“亮”点。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02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