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粉絲百萬“打賞”作者網絡文學“街頭賣藝”?
近日,來自國內某原創文學網站的一條消息引發關注,一位狂熱的鐵杆粉絲豪放地為自己的偶像作者送上1億網站幣(折合人民幣100萬元)的“打賞”,創下了網絡文學界有史以來粉絲“打賞”作者的最高紀錄。瘋狂的粉絲們開始在網絡文學界扎營了嗎?“打賞”盛行,網絡文學變成了“街頭賣藝”?粉絲經濟會成為網絡文學的餡餅還是陷阱?
“打賞”是一種赤裸裸收買文人的方式
驚聞有網友“打賞”自己鐘愛的寫手百萬元之巨,從事傳統出版多年的我,不得不感嘆這網絡世界、數字出版領域著實要刺激得多。類似“打賞”其實古已有之,最知名的典故當屬“千金買賦”。據傳當年陳阿嬌皇后失寵,為扭轉局面,豪擲黃金千斤請司馬相如作《長門賦》,此文成功打動漢武帝,佳人因此再獲帝王寵幸。
誠然,“打賞”文人的富商巨賈、達官貴人,歷朝歷代不乏其人,不論他們是一時興起,還是熱衷附庸風雅。但是,放到所有人群中去看,這只是極少數人的極個別行為。這樣的個案,跟文學的整體發展關系不大甚至沒有關系。個別人為自己喜愛的作者和作品揮金如土,不代表整個社會對文學普遍重視。即使百萬“打賞”真有其事,而不是炒作,也掩蓋不了當前文學邊緣化的尷尬處境,同樣否認不了文學創作的蒼白虛弱。隻有個把有錢人慷慨解囊,而沒有社會環境與文化制度的配合推動,要提振文學無異於痴人說夢。
當然,不能說這種“重賞”沒有鼓舞和激勵作用,在豐厚的利誘面前,肯定有大量的“勇夫”競相追逐。但是,這樣炮制出來的文字,有多少文學價值,是很成問題的。可以想象,這多半是一種迎合個別人或者某類人的狹隘趣味和特定喜好的文字,比如那些所謂文學網站上最流行的穿越、玄幻、修仙、奇情、靈異等題材創作,不用看也知道絕大多數是速朽的垃圾。
不僅如此,“打賞”甚至會傷害真正的文學創作。歷史上,多少文人在“打賞”下卑躬屈膝,他們為了一己私利,不惜歪曲事實,溜須拍馬,文字成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工具,文人也墮落成了權貴的家奴、幫凶。在某種意義上說,“打賞”就是一種赤裸裸收買文人的方式,它讓文學向權力低頭,向金錢妥協,褻瀆了文學的神聖性,培養了文人和作家的輕骨頭,其危害自古迄今流毒不淺。
需知道,文學從來不是“打賞”出來的。杜甫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學來自作家真情真性真良心的抒發,來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格不能獨立自主,思想與精神為他人所左右,是無法創作出真正的文學作品的,即便勉強炮制,也注定是過眼煙雲。在這個商業社會,我們習慣於把一切事物都當作商品,文學也不例外,當文學是商品,它是有價的,但真正的文學卻是無價的,而且往往名垂青史的沉澱為經典的作品,都不是“打賞”的產物,而是作家自發的創作。
所以,在我看來,這“百萬打賞”就當看個熱鬧罷了,人家有錢,有買有賣,無可厚非,旁人無權置喙,關於文學,它說明不了什麼,也改變不了什麼。不過,在這裡還是要奉勸那些少男少女粉絲,閱讀消費要理性,捧角要量力而行,與其沉迷於網絡文學,不如多讀經典作品。對有志有心的寫手來說,則應該有意識地保持潔身自好,自覺抵制別有用心的“打賞”,不被各種利益收買,是一個優秀作家基本的原則,是開展創作的底線。(受訪者:黃文杰,出版社編輯、傳播學博士。)
百萬“打賞”更像是一次商業營銷事件
在2009年的一次研討會上,作家麥家毫不留情地“炮轟”網絡文學—“如果我擁有了一項權力,我要消滅網絡文學。”“如果想從網絡上找到好的文學,無異於大海撈針。”麥家的言辭過於激烈,但是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網絡寫作市場的良莠不齊。一家傳統出版社一年的出版量也就在幾千萬字,而一家文學網站一天的產出量就與之相當,如此大的產出量,加之缺乏嚴格的把關機制,保質保量自然成了難題。
然而,在網上看書已經漸成潮流,並且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接受在網上付費閱讀,比如你想在網上閱讀一部小說,可以先免費閱讀一部分公眾章節,然后申請成為VIP用戶,付費閱讀剩下的VIP卷。它的收費很低廉,以每千字2分錢計算,閱讀20萬字隻需要4元錢,比紙質書要便宜得多。讀者點擊所得的費用由網站和作者按比例分享。
毫無疑問,付費閱讀對於網絡寫作的意義不可估量。它開創了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贏利模式,同時也使網絡寫作作為一種職業和生活方式開始獲得社會的認可,數以千計的作者靠網絡寫作謀生。
但是,就像演藝界一樣,懷有明星夢的年輕人一撥又一撥,可真正能成名的有多少呢?甚至目前都沒有權威的數據能夠顯示讀者的閱讀結構發生了什麼樣的改變,網絡文學到底佔到了多大的比例,網絡文學的讀者群和傳統有什麼不同,他們的收入層次是怎樣等等,所以,我更願從營銷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它更像是網站的一個商業行為,不太能代表這個行業的現狀及未來,大家都洗洗睡吧。而且,“打賞”、“撒花”等是互聯網比較多用的形式,並不是新鮮事物。(受訪者:閻蘇,外企職員,網絡文學愛好者。)
隻能期望讀者鑒賞水平能高些
在“打賞”成為網文界常見的一種“互動”方式時,100萬元隻不過在數字上高了點而已,況且,不排除有網站利用此消息來博宣傳。有網友就評論道,作者用另外一個ID給自己打賞一大筆錢,用來提升知名度,那筆錢也不過是從左手換到右手而已。
之所以把“打賞”稱為一種“互動”方式,是因為在讀者與作者之間,“打賞”維系的不只是一種金錢激勵關系,也代表了讀者對作者寫作水平或寫作風格的認同,對作者而言,“打賞”提高其收入是一方面的,更大程度上是,讀者通過這種方式告訴了作者,“我們喜歡看你這樣寫!”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打賞”和“評論”是同步進行的,而且,“打賞”成了“好評”的代名詞,因為沒人相信,一位讀者會因為不喜歡一位作家的作品而給他賞金,除非是開玩笑式的“給你五毛,趕緊滾。”
只是,由“付費閱讀”、“打賞”、“月票”、“更新票”等構成的網絡文學粉絲經濟,細想起來令人五味雜陳。表面看,讀者為自己喜歡的作者或作品埋單,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傳統作家余華寫了本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第七天》,不也照樣賣幾十萬本嗎?買他書的,也多是他多年來的粉絲。再者,文人羞於談錢、文學拒絕商業的時代已經過去,作家有必要過上體面的日子,錢從何來?當然得從粉絲那裡來,作家寫出作品,讀者為作品付費,這事兒顯得天經地義。
但之所以讓人覺得網絡文學的粉絲經濟讓人覺得不對味,深層次看,還是讓人覺得金錢並非像紙質書那樣,在作者與讀者的外圍打轉。在過去,一本書寫完就是完了,傳統作家雖然也會為了迎合讀者去寫,但起碼在構思、創作、乃至出版之前這個過程,讀者是沒法參與進去的。而網絡文學不一樣,讀者從作者一開頭,就可以參與進來,有錢的讀者可以通過“打賞”,明著或暗著指引作者朝著自己喜歡的路線去寫作,作者當然可以說,"打賞"歸"打賞",和寫作沒關系”,但真有沒有關系,鬼才知道,我不認為有多少作者可以拒絕訂閱率和“打賞”,去堅持自己認為的正確的寫作方向。
可怎麼辦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讀者自有他們自己的閱讀口味,根據網絡文學改編的電視劇如《甄嬛傳》等席卷熒屏,不得不讓人承認網絡文學跟當下人們的娛樂生活貼得很近,這也是網絡文學迎合讀者的一個結果。這個結果在更改著文學的結構,讓文學的定義在悄無聲息地發生著裂變,可滋養精神的文學和可供消費的文學,在當下正在進行互相撕扯,作為一名中年讀者,我自然更喜歡傳統一點的、有精神營養的文學,但若批評那些鮮活的、與時代同呼吸的網絡文學,也覺得有欠寬容。
粉絲經濟是網絡文學發展的最大驅動力,商業不斷改變人類生存狀態,對文學也是一樣無堅不摧。面對網絡文學的粉絲經濟,單說什麼文學的堅守是沒用的,隻能期望我們的讀者鑒賞水平能高些、再高些,為網絡文學指出一條明路,別讓網絡文學在最巔峰過后“死於非命”。(受訪者:韓浩月,文化評論人、網絡文學觀察者。)
一種新的閱讀消費模式產生
看到狂熱的網文粉絲豪放地為自己的偶像作者送上100萬元的“打賞”,不由令我驚訝,在我看來,這意味著一種新的消費模式的產生﹔雖然在網文消費的市場裡,這還是個孤例,但我想這個“石破天驚”的消息所寓意的絕不是一種消費的偶然性。
從幾年前的大型網文收費網站的季度營業額破千萬,到現在網絡文學的總產值已經突破10億元,網絡閱讀市場正以一種爆破式的發展與營收影響著傳統出版業,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全世界的出版業,電子版的陸續推出,都預示著在現代,閱讀市場正發生著巨大的轉變。新的轉變必然會帶來全新的閱讀經濟。《懸疑世界》就是看到了這個巨大的轉變與全新市場的契機,全面轉戰數字平台。
新的閱讀經濟正在成長,各類全新的收費模式正在產生,這些模式也會彼此刪選、淘汰,也會日趨成熟,這是新經濟(310358,基金吧)模式成長的必然,而真正屬於這個新經濟的最佳商業模式也必將會脫穎而出,它將與傳統模式截然不同,它將完全適合新經濟模式。
這個新閱讀經濟,可稱為“新讀者經濟”。因為它打破了傳統的,單一定價模式,趨向多元化,除了購買之外,被賦予更多消費體驗與消費情感,這無疑是嶄新與充滿未來的。我認為它預示著一個龐大的新市場,這個市場不僅屬於網文,也會屬於明星偶像或其他富有個人色彩與群眾情感色彩的消費—一個全新的市場,是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化所獨有的經濟模式賦予的市場。
“新讀者經濟”的獨特性在於讓作者與讀者之間不再間隔著鴻溝,而是更緊密地交互在一起,這從另一方面講,最直接地反映了市場需求,同時讓“情感”成為一種新的消費模式。
我個人看好“打賞”模式,因為它代表著現代消費的個性化,孕育著全新的模式與龐大的市場,也必將成為未來商業模式中的黑馬。(受訪者:周影,《懸疑世界》執行主編。)
(來源:廣州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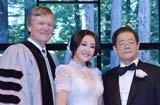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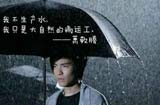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