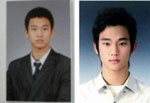如果木心先生還活著,昨天是他87周歲的生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繼2013年出版了木心紀念專號《溫故》特輯后,昨天又推出了《溫故》第二輯。本輯紀念專號首次發表了木心的《海伯伯》(未完成)、《如是我燈(序)》,並自諸遺稿中採擷精彩短句隨文編排,以饗讀者。陳丹青撰文《孤露與晚晴》,細述30年前“老小無猜,海外孤露”的紐約時光。
據悉,本期紀念專號除刊載了木心先生兩篇未發表的遺稿,還自手稿中選取了部分木心的短句。去年3月和8月分別在北京、上海舉辦的木心《文學回憶錄》座談會實錄,木心老畫友陳巨源回憶木心“文革”末期與出國前往事的專文,劉道一專訪台灣13位文藝人回顧木心自80年代以來在島內的持久影響,陳丹青的紀念專文《孤露與晚晴》,均為本期專號的亮點。
去年12月21日,木心先生逝世兩周年。繼去年的悼亡文《守護與送別》之后,今年,陳丹青寫成紀念稿《孤露與晚晴》,交代了木心故居紀念館及木心遺稿初步清理的工作,並首次披露木心在紐約恢復寫作的早期生涯。陳丹青在文中寫道,“木心死,及今快兩年了……他死了,這個詞一遍遍自動閃過,輕微而頻繁,好似無法關滅的信號。但刺痛襲來也不因這個詞,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動而鮮明。反倒周年忌日,無所感。人在種種規定的日子總會自我提醒吧,那是‘記得’的意思,不是哀傷。”
而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來,“初起著手《文學回憶錄》的工作,長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親在醫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慘苦,回家坐定,錄數百字,人即刻沉靜。此事前后八九個月,如今回望,隻一瞬,今年以來,則每月去一次烏鎮:晚晴小筑,將要辟為木心故居紀念館了。”
整理木心遺稿,“驚痛,鄭重,茫然,瞧著滿桌稿本,我又像是對著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幾十年來,我眼見先生開寫、修改、丟棄、重來,獄中所寫66頁手稿是他仔細折攏了,縫在棉褲裡,日后帶出囚室……兩年前,是的,就在這一天,我意識到木心遺棄了畢生的文稿。去吧去吧/我的書/你們從今入世/凶多吉少……那天下午是我最后一次面見活著的木心,又過六天,他死了。現在,我從遺稿中發現了以上短句。”
“這些凌亂而標致的手稿,部分寫在各種稿紙上,大部分寫在紐約文具店出售的筆記本,封皮留著價目的貼片……可惱的是,每首詩、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寫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頁面,實在難以判斷究竟哪篇是他所滿意的正稿。”陳丹青寫道,“然而手稿不是他。讀者想象先生,是書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學家’,我所牽念的,就是,孫木心。”
27年前,1987年2月14日,木心60歲生日,陳丹青回憶在新買的公寓燒了菜,給木心過生日,“早幾天我就問,選什麼花呢,他說,鳶尾吧,我便買了六株。那天好太陽,先生進來,看見花,說是蠻好、蠻好——瞧見花,他總會定睛一看,默默驚異——隨即取出一本灰藍封面的硬裝筆記本送給我,掀開首頁,便是這首四言詩——亡麟絕筆/尼父此心/奠麟奮筆/小子此悃/前叩名山/后禮其人/得枝桂角/渡河留馨/取湮眸白/取顯汗青/幸甚至哉/歌以詠誠。詩作讀畢,便是以下這行字: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滿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回憶那段與先生在紐約相處的時光,“那是我與先生頂開心的時光,老小無猜,‘海外孤露’。”陳丹青寫道,“兩年后,1989年,木心開講世界文學史,又23年,木心死,‘予滿甲子’,《文學回憶錄》出版了。此刻這本筆記本就在電腦邊,沒辦法,寫到這裡,我隻好掩面痛哭。”
據悉,本期專號特地選擇刊印了木心先生早期和晚期的若干繪畫作品,這些畫此前從未發表過。不久,將在木心故居紀念館展示。另外,經烏鎮及“木心基金會”的贊助與安排,去年一年,陳丹青與留守晚晴小筑的代威、昭明書院的匡文兵,著手將木心故居辟為紀念館,分別設置家族館、繪畫館、文學館,並擬今年2月14日木心先生誕辰日對外開放。由於施工人員春節返鄉,工程無法如期完成。目前各項工作仍在進行中,正式對外開放的確切日期,烏鎮與廣西師大社理想國網站將提前一周發布。
對話陳丹青
我是業余寫手,雖然被放在老是公開說話的情況
北青報:木心的《文學回憶錄》出版一年來,達到您當時的預期了嗎?
陳丹青:我沒有預期,隻有一個念頭,就是把先生留下的事做出來。當初2006年,他的十幾本書一下子出來,因為他老了,不可能像年輕人那樣一本一本出。他又非常小眾,文集上市是有壓力的,沒人買怎麼辦?所以我感謝年輕的讀者,沒想到會有這麼多70后、80后讀者。木心逝世那年,有形的讀者出現了,上百青年從各地趕過來送別。后來的情況超出預料。牛隴菲先生在網上持續追蹤100多輯讀者回應,逾百萬字,絕大部分留言表示驚訝——在我們的話語之外,有這麼一個人,這樣說事情,說學問,說思想,說文學。
北青報:有人說您對學術界對這本書的反應還是有些不滿的?
陳丹青:不是不滿,而是不知道“學術界”怎麼想,但譬如上海的孫甘露、陳子善、小寶,北京的孫郁、岳建一、春陽、李靜,都該是文學界學術界的吧,他們關注木心,幫我站台。但我不是要把木心放到哪個“界”,只是他老了,走了,我希望介紹給大家,這個“大家”,並不專指某個界。我從前屬於“美術界”,現在是單干戶,界內活動不知道,也不參加的。
北青報:您有聽到過一些負面的評價嗎?
陳丹青:北師大教授張檸寫過《木心,被高估的大師》,人大文學院舉行木心座談會,我就請他來,他來了,這才知道“高估”的題目是《羊城晚報》編輯刻意加上的,還有,他說他並沒有看過《文學回憶錄》。年底編木心紀念專號,會收入批評我罵我的網民留言,包括個別有名頭的作家。我知道自己惹人反感,但因此連累了先生。你不火,沒人理,你出頭了,要麼不理,要麼損你。這不單是對木心一人,而是普遍現象,你做點事,總有人說冷話。但張檸不是,他是職業批評家。
北青報:怎麼想到要整理木心的遺稿?
陳丹青:木心出名很晚,來不及出版他所有的文稿﹔而他出版書非常嚴格,所以我相信他有很多東西並沒發表。他生前,我不問這些事,現在他沒有了,遺稿怎麼辦?整理下來,比想象中多得多,直到他去世前半年都在寫,詩歌、短句,非常雜。我們非常困難,要甄別哪些發表過,哪些沒發表,最珍貴的發現,就是他出國前的部分手稿。
北青報:你為什麼要擔起這樣一個責任呢?甚至比你自己的寫作還要重要?
陳丹青:我失去了這位老朋友,我很愛他,敬重他﹔他如果名滿天下,像張愛玲那樣,有的是人去做,可是木心在國內文藝界唯一認識的人就是我,我不做,誰做呢?我是業余寫手,雖然被放在老是公開說話的情況,但這是媒體造成的,我平常就是畫畫,不是職業寫手,更不是文學家。
北青報:談到文學這個話題,在新媒體時代的處境似乎越來越艱難?
陳丹青:還是得有好作品。人需要文學,或別的學術書、娛樂書,但不管哪一類寫作,要寫得好,寫得好就會有讀者。八九十年代是文學的時代,新世紀是網絡時代,媒體時代,我不知道對不對,可是你看市面上有名的作家還是八九十年代出來的,但讀者群在改變,80后有了青春寫作,韓寒、郭敬明、蔣方舟等等,文學圖景變了,是跟著國家變化走的,可是80年代的重要文學家,今天仍然受關注,據我所知,像王安憶、余華等等,他們有新書出版,還是會有穩定的讀者群。
北青報:他們的新作您都看了嗎?
陳丹青:我不看小說20多年了,看不過來,太多了。我看書不分是文學或非文學,我看它寫得好不好。歲數大了,偏重歷史、傳記、專題,去年讀了楊奎鬆的《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我現在畫畫多了,又回到繪畫書的閱讀,《藍圍巾的男人》,作者是被弗洛伊德畫過的藝術評論家,中國沒有這樣的寫手。還在看法國老收藏家的《畫商日記》。我的文章反反復復說一個問題,就是——觀看。我關心這個時代我們怎麼觀看,怎麼看別人的“看”,那麼多圖像出來,怎麼看?中國尚未形成良好的觀看文化,還是文字國度,可是圖像時代已經到來。
文/本報記者 羅皓菱
(來源:北京青年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郎永淳與愛妻"生死相依"
郎永淳與愛妻"生死相依"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