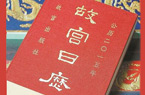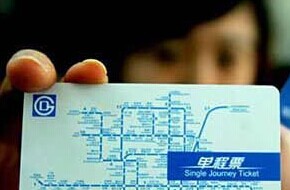張嘉譯、倪大紅
人民網12月31日電 (唐平)今晚,電視劇《大清鹽商》將在CCTV8開播。該劇開篇旁白道:“乾隆盛世,兩淮鹽業鼎盛,大清王朝四分之一的財政收入來自揚州。揚州城紙醉金迷,如同熟透的蘋果一樣異香扑鼻。”這麼些財富,在劇中集中體現在了以張嘉譯扮演的主人公汪朝宗為代表的四大總商身上。那麼歷史上,汪朝宗的原型鹽商江春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這麼說吧,姜文在新片《一步之遙》裡,諷刺了以武七為代表的“new money”,認為這幫人除了錢,空無一物。那麼江春此人絕對是一“old money”。有人這樣總結揚州鹽商的特點:“富甲天下﹔以商人之身結交官府乃至天子以保富貴﹔廣交天下文人以彰名聲﹔修園林,資戲劇,養庖廚以享生活。”
能聚財 會養財
江春自22歲投身商界,協助父親於揚州經營鹽業,直至69歲去世,前后40余年一直馳騁於兩淮鹽業,成為清代兩淮鹽業中的巨頭。江家究竟有多少鹽業資產與家產,史籍沒有記載,已無可考,但估計不下千萬之巨。
在傳統專制社會,這麼多的財富,要想保全可不是一件易事。自古官商一家,商業經營得好,首先就得有官家庇護。江春非等閑,一攀就攀上了帝王家,在歷史上留下“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美名。江春擔任兩淮總商的40多年裡,乾隆六次南巡,兩次東巡至天津等地,所資費用皆由他一人張羅操辦,他三次上京恭祝皇太后萬壽大典。為討得聖上歡心,“殫心籌策,靡不指顧集事”。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南巡,江春便“營繕供張,纖細畢舉”。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江春修治虹橋東之江公園,得到乾隆的贊賞。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乾隆在第五、六次南巡中到了江春的康山別業,嘖嘖稱贊。為了迎駕,江春大力修繕行宮園林,作為乾隆休憩游樂之所。據《揚州行宮名勝全圖》記載,江春一人建造的樓廊、亭台就有302座之多。
《大清鹽商》中再現了《清朝野史大觀》中江春為迎駕乾隆南巡在揚州瘦西湖“一夜造白塔”的傳說。傳說中,乾隆皇帝下江南時,來到瘦西湖時,他認為此處景色與北海“瓊島春陰”類似,只是少了一座白塔。隨駕的江春將這段話記在心裡,又用重金賄賂皇帝近侍,求得一幅喇嘛塔形狀草圖。是夜,江春找來能工巧匠,以鹽包為基礎,以紙扎為表面堆成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游瘦西湖,被一夜建成的白塔震驚,“人道揚州鹽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虛傳。”
這些巨額花費可不是有去無回的。因討得乾隆歡心,江春在乾隆三十一年被賜布政使銜,薦至一品,並賞戴孔雀翎,成為當時鹽商中僅有的一枝孔雀翎。有了官銜,對於這種級別的商人來說可就不一樣了,生意上順風順水那是必須的。
即便是出了事兒,也有皇帝撐著。乾隆三十三年,江南鹽引案發,江春遭受巨大打擊,三十六年,江春“家道消乏”,乾隆賞借他30萬兩皇帑,以資助他營運鹽業﹔五十年,又一次賞借25萬兩給他,按一分起息﹔五十八年,江春之子江振鴻“生計艱窘”,連皇帝曾經住過的康山花園都“無力修葺”,還是乾隆出面讓眾商出銀5萬兩,自己又令賞5萬兩,作為營運資本,“以示體恤”。
看來,做富商當如是啊!找棵大樹好乘涼!

張嘉譯
有責任 能擔當
做一個合格的富豪,隻為皇帝一人服務肯定是不成的,帝王心懷國家社稷,必要時還得為帝王分憂。即大工大役之時,要懂得“急公報效”。
拿江春來說,根據嘉慶《兩淮鹽法志》記載,先后與他人合捐。乾隆三十八年,捐平金川軍需銀400萬兩,五十三年,捐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軍費銀200萬兩,四十七年,捐濟水災銀100萬兩,三十六年,捐皇太后八旬壽筵銀20萬兩,四十五年,捐備賞?之用銀100萬兩,七次中,江春與他人共捐銀1120萬兩之多,佔到前面提到的乾隆幾次對邊陲用兵經費的十分之一。
《大清鹽商》中有一幕描述洪澤湖泛濫,加之連日暴雨,揚州潰堤在即,險情刻不容緩,為保全城百姓安全,汪朝宗冒著欺君之罪,私自從上繳的虧空稅銀裡挪出百萬兩修壩筑堤,並親自指揮河工們修堤筑壩,終因體力不支昏倒。最后部分,在揚州水災后的疫情基本停當后,汪朝宗准備變賣康山草堂籌款,以救百姓,這些情節無不是為了表現大清鹽商有社會責任感,勇於擔當的精神作風。或許這才是真正的富豪應有的品質吧。
懂生活 有品位
除在政治、經濟上外,兩淮鹽商在文化上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兩淮鹽商大多本身就極富才學,並與文士學者建立了或深或淺的聯系。江春的詩才曾博得過袁枚的贊賞,據《揚州畫舫錄》記載,江春 “工制藝,精於詩,與齊次風、馬秋玉齊名”。同時,他也多結交、延攬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常滿,亦一時盛也”。才高藝精的揚州八怪也常常成為兩淮鹽典富商的座上賓。電視劇中,對汪朝宗與鄭冬心(原型即鄭板橋)的交往多有著墨,亦是為了體現揚州文化之繁榮,富商對文化之敬畏與禮遇。
清代戲曲昌盛,揚州又是當時戲曲發展的中心。各色曲藝匯聚揚州,相互融合。揚州鹽商組織了七大內班,江春又征有花部春台班以備大戲。正是這兩淮鹽商征召的花部徽班於乾隆五十五年及嘉慶年間相繼晉京匯演,才有了我們的國粹——京劇。
除繁榮文化事業外,大清鹽商的個人生活亦是相當有品位、愛享受。
《揚州畫舫錄》中曾經屢屢提到揚州鹽商奢侈的消費風氣:選美選膩了,開始選丑,大姑娘大熱天在臉上涂醬油,在太陽底下暴晒,比誰更丑些。這在電視劇開篇中即有表現。比有錢,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集體跑到鎮江金山的寶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誰家的金箔第一個飄到揚州。當時還有個名詞叫“揚氣”——“什麼東西奢華、講究到極致,就是揚氣。”
在飲食上,揚州鹽商為世人留下了淮揚菜這一遺產。明清時,豪富的鹽商蓄養著來自各地的名廚,一到吃飯時,廚師要准備數十道菜,主人先看色澤,再品味道,而且,鹽商之間時常會“斗菜”。這種競爭的氛圍中,菜肴越來越精細,淮揚菜通行天下。在電視劇中,總商鮑以安講述自家的雞蛋是由蒼參喂養的母雞所生,在歷史上確有其事——總商黃鈞泰家的雞飼料由參術耆棗等研細加工而成,每枚雞蛋價值白銀一兩。這一枚雞蛋抵得上農民的三石稻谷,揚州鹽商之生活奢侈可見一斑,同時也可見得他們生活的品位。
能聚財,會養財﹔有責任,能擔當﹔懂生活,有品位,這基本反映了大清鹽商富豪們的基本面。能得一項者易,而將其三兼得,可不是容易之事。大清鹽商之“豪氣”才可見一斑,絕不是這些“old money”可比。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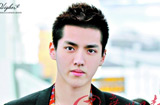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