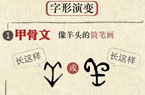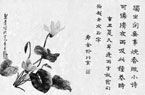■ 反映日本與清政府之間戰爭的浮世繪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周建高
從明治時代到二戰戰敗的近代日本意見領袖德富蘇峰(1863-1957)根據“科學的歷史眼光”,認為大東亞戰爭“從心裡相信是義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言論呢?
19世紀日本在被迫卷入條約國際體系不久,就把不平等條約體系強加給亞洲鄰國,走上對外擴張侵略的帝國主義道路。二戰結束至今已70周年,但對戰爭的認識分歧,依然是影響東亞國際關系的“老毛病”。為什麼至今仍有許多日本人不承認侵略,我們解剖一下日本近代以來的文明觀,或許能找到鑰匙。
效仿歐美的“文明開化”
明治維新使日本從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急劇邁進。用一個當時流行的詞概括,就是“文明開化”。它與“自由”、“人權”、“獨立”等一樣是當時流行的新概念,洋學家們紛紛刊文立說。在傳播文明的學說中,福澤諭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概略》是最系統完整的著作。他1872年發表《勸學》,以“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一句開篇,立刻獲得社會極大歡迎。在當時3300萬人口的日本累計銷售340萬冊,創造了空前的銷售記錄。福澤沒有出仕,但政府高官常向他請教,他的著作被作為學校教材廣泛流傳,他成為近代日本影響最大的一位啟蒙思想家。
歐美為文明,土耳其、中國、日本為半開化,非洲、澳洲為野蠻,福澤在《文明論概略》中描繪的這幅世界地圖,是19世紀后半葉歐洲流行的觀點。當時西方勢力在全球所向披靡,亞非拉各大洲許多古老國家淪為殖民地。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中國被迫向西洋蠻夷割地賠款,顯示出清國的衰敗。日本人認識到東洋在武備、貿易、學術各方面都不如西洋。不平等條約使洋人在日本享受著特權、仗勢欺人。日本要擺脫被殖民化的危機,保持獨立自尊,隻有走向歐美那樣的“文明開化”才能富強,與西洋諸國並駕齊驅。日本與歐美存在“半開化”與“文明”的差距,這種認識是近代日本以歐美為標准自覺舍己從人的心理基礎,成為文明國家是日本現代化的根本動力。
重智輕德的文明觀念
近代西方的文明,指物質上如衣食住行乃至戰爭工具的發展等,精神上脫離中世紀的神學統治而思想啟蒙后個體精神的獨立、理性和社會關系上的自由、平等乃至憲政等。文明概念傳入日本后發生了變異,在促進社會進化的同時,也成為為侵略擴張辯護的遁詞。
福澤諭吉把文明歸納為“人類智德的進步”。他認為,智是指思考、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智分私智和公智,私智指機靈、明白利害,公智指觀察形勢、分辨輕重緩急的才能。道德隻存在於個人內部,德也有私德、公德之分,前者指內心活動如純潔、嚴肅等,后者指社交道德,如廉恥、公平、勇敢等。古人說的溫良恭儉讓、仁者樂山等都是私德,私德的功能是狹隘的。
在福澤的文明觀中,智先於德、優於德。“拿智慧和道德相比較,認為智的作用是重而廣的,德的作用是輕而狹的”,“德和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無智的道德等於無德”。在公智私智、公德私德四者中,公智最重要。研究物理、機械等學術,或像亞當·斯密那樣研究經濟規律,將知識成果傳播四海,給人類貢獻了無數福祉。道德的性質千古不變,智慧則日新月異。私德如同鐵材,智慧如同加工,同樣材料加工成不同的東西,貴賤不一,不同加工得到的附加值不同。野蠻時代,道德支配人間關系﹔文明時代,智慧支配人間關系。日本的燃眉之急是智慧不足,文學、技術、商業、工業等沒有一樣能與西洋比較。“文明的真諦在於使天賦的身心才能得以發揮盡致”,人們獨立自主地從事生產經營、學術研究,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福澤的宗旨就是要日本人改變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官尊民卑的習氣,不因襲往古,自由思想,發揮才智,推動日本前進。
近代日本重智輕德,側重發展經濟、軍事。通過教育敕語宣揚的道德,以忠孝為核心,鼓勵國民“義勇奉公”,為天皇和國家不惜犧牲自己,缺少西方文明中對於個人利益的尊重和保障。近代日本文明觀中,追求利益是天賦人權,弱肉強食是自然規律也是社會規律。侵略朝鮮、中國這樣貧弱的國家,從文明觀看,屬於遵循社會法則,以文明開導愚昧。於是日本人解除了道德負疚感,甚至有了替天行道般的大義凜然。二戰中日本戰敗,對於戰敗的原因,多數日本人並不認為是因為本國發動的戰爭是不正義的,而認為是實力不如人家,不該在沒有充分准備的情況下挑戰美國。親身經歷了明治時代到二戰失敗的日本言論界領袖德富蘇峰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對外戰爭“問題既不是正邪的問題,也不是是非的問題。關鍵僅僅是強弱的問題。”“文明”、“進步”而非道德成為近代以來日本人的行為准則。這種價值觀是日本與亞洲國家在戰爭問題上產生分歧的根本原因。
不擇手段的國家至上
近代日本的文明觀中,為了達到於己有利的目的,手段不必拘泥。
福澤諭吉認為,狹義的“文明”是指單純以人力增加人類物質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裝飾,廣義上是指不僅追求衣食住享受,且勵志修德,把人類提高到高尚的境界。但他所謂的“高尚”並非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舍己為人之類的道德,而是積極參與社會交往、關心國家大事,改變消極被動、與他人不交往的狀態。他有時把文明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人類前進的終極目的,稱文明至大至要,能促進文明的就是利,使文明退步的就是害。他認為:“社會上的一切事物,可能有使人厭惡的東西,但如果它對文明有益,就可不必追究。譬如,內亂或獨裁暴政,隻要能促使文明進步,等它的功效顯著表現,人們就會把它往日的丑惡忘掉一半而不再去責難。”但更多場合,國家利益才是日本知識人的最高目標,文明不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福澤諭吉宣傳自由、平等、獨立,鼓吹一身獨立則一國獨立。在他文明論中,“自由”“平等”的分量不多,而“獨立”是他關注的重點。他所謂自由,是要日本人改變自古以來官尊民卑的心理,盡自己所能參與國家建設﹔所謂平等,是希望日本國內的官民權利平等,讓百姓、讀書人可以參與國家輿論。所謂獨立,是鼓勵歷來依賴俸祿生活的武士階層在失去特權后自食其力,積極參與殖產興業,同時爭取日本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他要日本人首先人人謀自己獨立,然后國家才可安泰。“國家獨立是目的,國民的文明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手段有無數的層次,越多越好,而且非多不可。希望日本人“劃清內外的界限”,對外要堅決與外國人“爭利爭理”,把“日本國締造成一個兵力強盛、商業繁榮的大國”。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文”與“武”相對而言,指溫柔、和平,文明的對立面是暴力、戰爭。侵略這種損人利己的戰爭不道德也不文明。但近代日本思想中,戰爭是文明題中應有之義。福澤諭吉說國家關系隻有兩種,平時進行貿易互相爭利,否則就是開戰互相?殺。“戰爭是伸張獨立國家的權利的手段,而貿易是發揚國家光輝的表現。”貿易、戰爭都是文明的內容。他提出,討論事物的得失利弊時必須考慮時間性(時代)和空間性(地點)。沒有絕對的善惡利弊,必須考慮具體環境,包括戰爭。他稱,“戰爭固然是壞事,但對敵人卻不能不戰。殺人固然違反人道,但在作戰的時候就不能不殺人”,“天地間沒有貫穿一切事物的道理,隻能是隨著時間和空間來進行觀察”,因此他是對外擴張的積極支持者。
國家利益至上,是日本近代各種思潮的共同點。自幕末權利概念傳入后,明治初年日本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自由民權運動,批判政府專制,要求設議會、立憲法。但在國際關系上,民權派轉身擁護國權而支持政府。近代以來,日本從西洋輸入各種思想,出現了各種政治經濟黨派,但一旦遇到國際紛爭,無不支持對外強硬。一貫以在野立場批評政府的福澤諭吉,在甲午戰爭爆發后欣喜若狂,認為並非日本侵略,而是謀求文明、開化與進步的日本討伐阻礙進步的清國,將文明事業推向亞洲的行為。而原本倡導平民主義、和平主義,堅決反對軍備擴張和侵略主義的德富蘇峰,在甲午戰爭開始后,通過報刊積極支持出兵,煽動戰爭熱潮。20世紀初,輿論主張“對外實行帝國主義,對內實行立憲主義”,認為以文明國統治野蠻國之土地,為天演上應該享受的權利﹔以文明國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是倫理上應盡之責任。可以看出,近代日本思想中,文明是追求、擴大國家利益的手段,被作為對外擴張的幌子。
不願擔責的戰爭辯解
在近代日本人觀念中,文明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實際的存在,文明模范就是歐美。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開篇就號召日本人不僅在有形的物質領域,而且在無形的精神、價值觀方面,都應以歐美為榜樣,即所謂“脫亞入歐”。對歐美亦步亦趨,是日本近代史的軌跡。明治以來的各種主義,從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無一不來自歐美。作為后發展國家,日本因其善於學習而后來居上。二戰失敗,日本戰犯受到國際審判。雖然基於現實主義考慮,日本服從美國為首的戰后世界秩序,但是對於東京審判質疑、不服的聲音始終不斷,對那場戰爭的反省,也是意見紛紜。有人從感情上不願承認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不願承認日本是侵略國家﹔有人認為日本無罪。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旗手,1945年已83歲高齡依然擔任著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大日本文學報國會會長的德富蘇峰,在戰敗后反省歷史時說道,即便從日美關系史的梗概也可看出,太平洋戰爭是出於不得已,戰爭是歐美人刺激、教唆、誘導、挑舋日本人而導致的。要說戰爭責任,全體日本人都有責任,標榜人道主義、文明偉大先驅的歐美人也有責任。這種論調的邏輯類似於一個十幾歲少年,是精神不成熟的表現。
近代以來,日本較快地吸收了歐美的科學技術、產業方式,實現了富國強兵,沒有像其他亞洲國家那樣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定程度上“脫亞”成功。經過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躋身世界強國,與歐美並駕齊驅,也可謂“入歐”。但國家和社會制度、思維方式、國民精神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西化。自由、平等、尊重人權,這些近代文明的核心理念,近代日本無論在國內社會關系還是國際關系上都沒有很好實踐。其吸收的西方文明,只是那些有利於增強力量、獲取權益的部分,物質進步顯著而精神則古今混雜,即在現代概念外衣下保存著恃強凌弱的原始獸性。福澤諭吉1860年隨團考察美國途徑香港時,十分羨慕英國人壓制中國人,期待日本富強后不僅要像英國人那樣指使中國人,更要像對待奴隸般壓制、束縛英國人。他直言不諱壓制別人可謂人間最大之愉快,當前有外國壓制日本,“我等之志願,在於壓制此壓制,並致力於獨自在世界中推行壓制”。英國哲學家羅素評論日本道,日本人批評白人把其他文化都看作低等文化,自私而損人利己、得寸進尺,為了金錢不擇手段,這是公允的。人們也許會認為日本人會盡力不學白人。然而“實際上,隻要是歐洲人對中國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過,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跌宕起伏的時期,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令人權觀念得到發展和普及。以武力解決國際紛爭為道義和法律所禁止,侵略行為成為“過街老鼠”。戰后日本整體上成為和平主義者,但右翼勢力總是否認歷史上對外戰爭的非正義性,認為日本不過學歐美文明國家的樣,興兵海外乃“解放亞洲”的道義責任,並把戰敗責任歸咎於外界。這就像經營者把生意失敗歸咎於競爭對手、歸咎於自己跟從的師傅那樣,是缺乏責任感、不成熟的表現。
日本近代以來之所以走上侵略擴張道路,根源於東施效顰的文明觀,或者說文明成了追逐國家利益的幌子,而忽略了文明真諦的自由、平等、博愛。但不管他們怎樣辯解,判斷罪與非罪唯一的根據是侵害的事實或行為是否發生,即使過失犯罪也得承擔責任。何況日本的戰爭罪行是國際法庭早已判明的。無論到何時,隻要不坦率地、勇敢地承擔戰爭責任,就說明日本精神上尚未成年,就難以被作為國際社會普通國家的一員獲得認可和接受。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