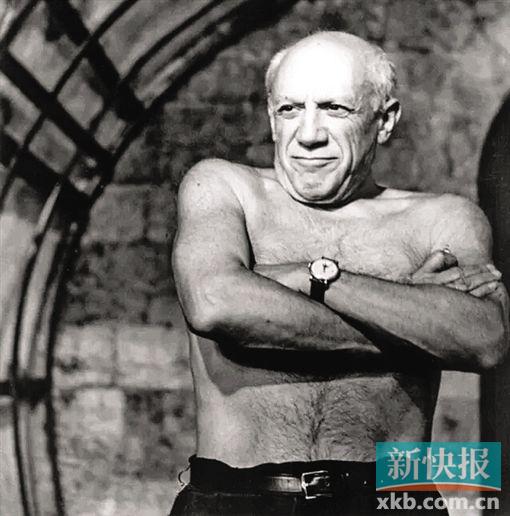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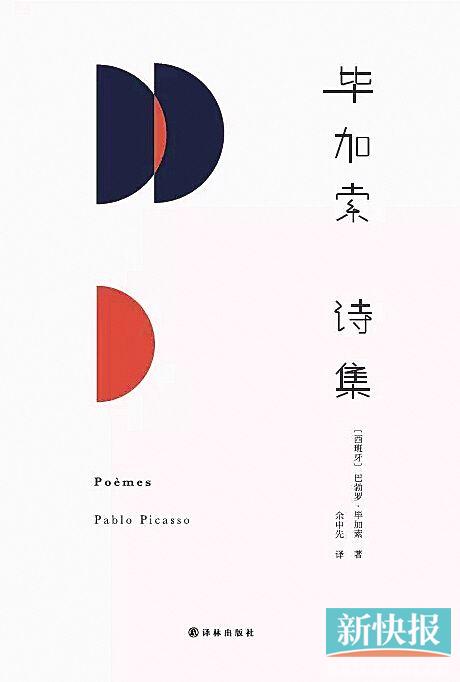
《畢加索詩集》 作者:[西班牙] 畢加索 譯者:余中先 譯林出版社 2016年2月
如同他的作品一樣,要讀懂他的詩還真要費點勁……
除了畢加索一輩子的各種顏色階段和每個階段裡跟不同妹子的風流韻事,你可知道,這老頭兒還寫得一手“好詩”。1935年,54歲的畢加索開始了寫作,他自己的說法是:“丟下一切,油畫、雕塑、版畫、詩歌,來全身心地投入於唱歌之中。”然而他並沒有真的去唱歌,從1935年到1936年,他幾乎每天都在寫詩!
無標點符號的詩
對我們來說,讀到畢加索的詩歌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他用西班牙語和法語寫作,法語稍多,有時候,他會在一首詩的內部混淆使用這兩種語言……畢加索歡樂地暢游於兩種語言之間,連續寫了幾首西班牙語詩歌之后,便換作用法語寫詩,順便聊了聊自己對於“翻譯”的思考(他大概也覺得別人翻譯自己的詩歌真的很難):
“假如我在一種語言中思索並寫下‘狗追著兔子跑在樹林中’而我想把它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就應該說‘白木桌子把它的腳爪陷入在沙土中擔心知道自己竟如此愚笨而幾乎嚇死’
(1935年10月28日)”
從上面這一首詩歌裡,你應該看出兩個問題:
第一:咦?是有人把畢加索的詩歌翻譯成中文了嗎?
是的,曾經翻譯過薩岡、昆德拉、貝克特的翻譯家余中先先生做到了!在讀詩譯詩的過程中,他說自己“大為驚訝,一驚再驚,大呼過癮,欲罷不能”,“畢加索詩如畢加索畫,也如詩人畫家其人,想象豐富,詞語奇怪,形象詭異,邏輯混亂,很有立體意味”。
第二:Excuse me?畢加索的詩裡都沒有逗號和句號嗎?
其實是有的啊,隻不過非常非常少而已……譯者余中先這樣說:“他的詩歌基本上沒有標點符號,隻有極其個別的一兩處有逗號,還不知道是不是筆誤。”
無規則可言的詩
雖然,畢加索在上世紀60年代向朋友提出了一個十分謙虛、真假難辨的反問句:“說到底,我是一個寫得不好的詩人。你不認為嗎?”
但在畢加索的內心,他大概是拒絕通常意義下的語義學規則和詩歌標准的:“假如我得按照那些跟我毫無關系的規則來修正你說到的錯誤,那麼,我所特有的音符就將消失在我並未領悟的語法中。我寧可心血來潮自作主張地造它一種語法,也不願讓我的詞語屈服於並不屬於我的規則。”
譯者余中先覺得,如果我們以挑剔的眼光做認真細致的分析,畢加索的詩歌不是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也不可能留下太重要的痕跡,但是“他在詩歌這一書寫形式上留下的種種嘗試,讓后人更加明白理解到他的繪畫藝術(造型藝術)的創造思路”。
余中先說,“如果我們的想象力能把畢加索詩歌中隱藏在單一方向的線性文字背后的意向化為二維(甚至三維)的圖畫,那麼,線性的文字中種種色斑與線條的鋪陳,就會讓我們不由得更多地聯想到空間中的物件的碎片和多變的點彩的奇特分布。這恐怕就是畢加索詩歌的藝術價值所在。”
風格“清奇”的詩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畢加索詩歌,隻能說:這詩風很“清奇”呀,不信你看:
“大蒜以它枯葉星星的顏色在笑
由其顏色深扎的匕首以它嘲諷的神態笑那玫瑰
呈枯葉的星星的大蒜
正下落的星星的氣味以它狡黠的神態笑那玫瑰的匕首
呈枯葉的
翅膀的大蒜
(1936年6月15日)”
讀畢加索的詩,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余中先/文(有刪節)
畢加索向來就不局限於唯一的藝術創作方式。最熟悉他的創作才華的母親,曾這樣說到她的兒子:“有人告訴我說,你在寫作。你嘛,我知道是什麼都能做得出來的。假如有一天有人對我說你在主持彌撒,我也會相信的。”當1935年他在法國開始寫詩時,已然五十有四。1989年,法國的伽利馬出版社出版了畢加索幾乎全部的文字(還包括一篇關於詩人畢加索的傳記),普通讀者才驚訝地發現,這位大畫家原來還從事著“一種始終陌生卻又持續了多年的文學活動”。
詩畫不分家
那麼,他的詩有些什麼特點呢,或者說,他的詩是不是與他的畫有一些內在的關聯呢?中國人老愛說“詩情畫意”,傳統的文人更是“詩畫不分家”,而這一點,在畢加索的身上其實體現得很有些意思。
畢加索的詩歌創作恰如他的繪畫,具有一種驚人的多樣性和實驗性。用這位詩人畫家的話來說,“總而言之,凡藝術必為相通;人們可以寫出一幅詞語的畫來,恰如人們可以在一首詩中畫出種種的感覺。”
確實如此,讀畢詩,譯畢詩,讓我大為驚訝,也讓我大呼過癮,欲罷不能。畢詩如畢畫,也如畫家其人。
他的不少詩一氣呵成,沒有反復,后來也沒有作修改:那是一些“江河詩”,字詞在詩行中擁擠,恰如“物體”在繪畫中擁擠。這些詩歌,如一股奔流不息的洪流,根本無法標點,讓人閱讀時不得不依照一種隨呼吸而生成的節奏。例如這段:“精確的再現刻寫在空無的今天下午的雨滴的寂靜的沙粒上鋪展在一個蠟像的羽毛床上的內衣上模仿著在一條河邊嬉戲的小孩子他用一根李子樹的枝條戲弄著兩隻坐在其陰影的洗碗槽上的土豆皮上的蟑螂……”(1938年2月12日)
另一些詩,則被寫成具有多樣性的語態,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句斷嘗試,構成不同的詩行和詩節,或是某種散文形式。從它們對音節結構、音樂性,甚至還包括對押韻的考慮來看,能見出這是一種更為經典的詩歌創作:“夜//在泉池中//夢扭彎角喙//叩擊空氣//掙脫顏色的腸衣……”(1935年12月30日)。
滿滿的色彩
我們應該記得,畢加索的畫往往讓濃墨重彩大紅大綠的色塊反復出現,反復地沖擊人的視網膜,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的詩也如他的畫一樣,試圖以碎片狀的物品佔據空間的各個部分,各個層面。他的詩歌中有大量的顏色詞匯,而色彩,還有種種細微的色調差別:紅有莧紅、玫瑰紅、火紅、血紅、磚紅、胭脂紅,藍有國王藍、石油藍、天藍、鈷藍,綠有杏仁綠、蘋果綠、青綠、祖母綠,等等。
例如以下幾段(詩句中並無標點):
“再現那個姑娘腦袋樣子的繪畫去除了所有線條周圍飄飄蕩蕩地顯現白色的芳香陣陣打擊落在天空的肩膀白色的驕傲奶酪大麗花白葡萄酒油炸在白色吹短笛者的泥鴿射擊場鞭子的黃色叫喊被一隻燕子的飛翔反射在紫色乳汁的眼睛上?麻飛馬在黃裡帶白的泡沫的盡頭紫色長矛的胸衣鉛筆跳山羊的線條白色的星星紫裡透黃躺在月亮的刀鋒上紫色小粒菜豆菜弓弦繃張在黃中透藍的鳶尾花鈷藍靛藍在留有透藍白羽毛的黃色石板瓦的紫色網中繩索套上帶鴿子黃的淺紫脖子藍色的奶子砍去了腦袋還咬著泛黃的湖水紫色的手白色的嘴唇藍色的假領老鼠啃吃紫色黃色藍色的麥穗紫色黃色藍色藍色藍色藍色線條纏繞它的螺旋大橋拉長氣喘吁吁地第一個到達靶子的中心”(1936年4月29日)。
讀到感覺沒?
另外,畢加索的某些詩歌寫得如同字謎,例如“我的女士開心笑沙”(1936年3月24日)的讀音(ma lady gai rit sable)與“可治愈的病”(maladie gu?rissable)一樣。在畢加索筆下,相似詞形、相同發音的字詞常常在同一個詩句中同時出現,構成或有趣、或別扭、或艱澀、或轉義的文字游戲。
作家米歇爾·萊裡斯說,他隻見過一個作家,“可以當之無愧地與畢加索比肩而立,試圖將自己定位於字母的版圖繪制術中”,“此人就是詹姆斯·喬伊斯,他在《芬尼根守靈夜》中,証明了一種相似的能力,能推進語言成為現實的東西(人們是這樣說的),現實得可以被人貪婪地吃掉喝掉,並被人令人眩暈地自由使用”。不知道這一評價畢加索是否當得起。
畢加索的詩還是值得一讀的,哪怕有的人讀后會覺得莫名其妙。欣賞他的畫,對觀眾來說不是懂不懂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感覺的問題。讀他的詩歌也是如此,問題在於,你作為一個讀者,有什麼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