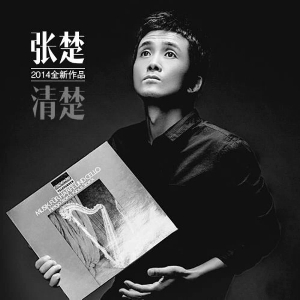
null
那個唱著《姐姐》、《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的張楚,那個“魔岩三杰”之一的張楚,那個“游吟詩人”張楚回來了,日前他的新歌《到達》、《海邊》、《晃動一下》已經上線音樂平台,5月27日他還將帶著自己的“微小相見”全國巡回演唱會來到廣州星海音樂廳。這不是張楚第一次來廣州開唱,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就來過廣州找撈仔做編曲﹔接受信息時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張楚還透露自己的“姐姐”就生活在廣州,外甥就算是廣州人。
張楚身上有許多許多的標簽,1994年在香港紅磡舉行的“中國搖滾樂勢力”成為太多人的青春坐標,但他本人早就不太願意在現場唱《姐姐》,不願意總是被和“魔岩三杰”、“西安三杰”捆綁在一起。帶著全新的作品和全新巡演重新出發的張楚,還是說著思維跳躍並且飽含哲理的話,好在是他終於又有了新作品、又出來唱歌了﹔他不願意被稱作“詩人”,他認為“詩人”這個標簽沒有意義,他說自己就是一個獨自認真生活的人,一個尋求自己快樂的人。
□專題撰文 信息時報記者 丁慧峰
對廣州的舊印象:
汽車開得很快,不懂他們追尋的未來是什麼
不喜歡用“老炮兒”來形容張楚,但他真是中國搖滾樂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性人物,尤其1994年和竇唯、何勇、唐朝等在香港紅磡舉行的“中國搖滾樂勢力”演唱會,幾乎象征著中國搖滾樂最為輝煌的高度。而“魔岩三杰”更成為很多人的搖滾記憶。
不同於竇唯的酷和何勇的狂,張楚顯得沉默、木訥,一個人穿著格子體恤衫坐在椅子上唱《螞蟻螞蟻》的畫面,被銘記在很多人的頭腦中。有關那次演唱會有太多傳說,比如何勇說出了“四大天王除了張學友都是小丑”,比如說黃秋生自己撕爛了衣服在現場狂奔(恰巧近日黃秋生自己在微博否認了,說自己當時穿的是皮衣),而竇唯說起當年充斥著“陰謀”,更有“無需紀念”的言論。
張楚就顯得低調很多,並且自1994年之后,僅出版了一張《造飛機的工廠》就消失了,后來還有何勇說“張楚死了”,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張楚很長一段時間消失不見。離開北京,也離開喧囂的樂壇和搖滾圈,回到老家西安,甚至一段時間在青島隱居。僅在2004年,張楚為數不多的出現,到廣州參加“廣州新年搖滾音樂會”。而這次的“微小相見”,將是張楚第一次來廣州舉辦自己的專場演唱會。
說起廣州,張楚一點都不陌生,直言“對廣州這座城市太有深刻印象了”,他說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曾到廣州找吉他手撈仔做編曲,當年印象最深的是這裡的汽車開得很快,那個時代也是廣州最繁忙的時代,“汽車非常匆忙得從你身邊過去,有一種很震撼的感覺,不懂也看不清他們追尋的未來是什麼”。
張楚說另外一個感覺是廣州很美,有很多很多的樹,花開得很漂亮,還有一些古建筑,“北方人一說廣州很容易說到香港,實際上廣州有非常傳統和質朴的文化”。
不想再唱《姐姐》:
歌迷呼吁的話盡量回應,粵語歌聽得不多
《姐姐》是張楚的代表作,更是中國搖滾樂能夠排進前十,甚至前五、前三的作品,地位相當於《一無所有》之於崔健,《鐘鼓樓》之於何勇。直到現在《姐姐》的旋律和張楚的嗓音突然想起,還是會讓不少文青突然悸動頭皮發麻乃至流淚,但是張楚本人卻很少在演唱會唱這首歌曲了。
被問及來廣州星海音樂廳如果台下歌迷反應太過熱烈,大家一起“起哄”高呼《姐姐》會否演唱,張楚就笑說:“盡量回應吧,反正也是一次交流。”而對於歌迷聽到《姐姐》痛哭流涕,他就說:“不會驚訝,也不會反感,希望淚水是美好的淚水,而不僅僅是因為感懷。”
如果單純從歌詞理解,《姐姐》講述的是一個蠻為悲壯的故事,觸發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鳴。張楚本人在接受《魯豫有約》採訪,畫面中有一幅張楚收藏的油畫,一個小孩和姐姐打扑克的畫面,張楚說能讓他想起小時候和姐姐玩的場景,可見姐姐對張楚的影響。
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張楚意外透露自己的姐姐就生活在廣州,外甥就算是廣州人,感覺他們用粵語說話是另外一種文化,有專屬於自己的情感。對於來廣州會否唱一兩句粵語歌,張楚就笑說可以找個人現學,把自己的一兩句歌詞改成粵語,但坦承自己對粵語歌情感聯系比較弱。
張楚說自己作為北方人,粵語歌聽得不多,“感覺粵語歌真的是沒有好的作品,我自己聽得好的也就是達明一派,因為他們音樂做得好,所以就愛聽,別人的就聽得特別特別少”。對於代表粵語搖滾樂的Beyond,張楚也說關注不多,知道他們是很成熟的、商業品質很好的樂隊。
張楚說其實不單是粵語歌,近些年國語歌聽得也不多,當然知道有一些很不錯的新作品,但去Livehouse自己喜歡看的還是國外的樂隊。張楚說近十年的中國搖滾樂是“奇觀”的十年,因為沒有真正去展示個性,不說自己最真實的東西,不太像西方搖滾樂的表現方式。
新作品自己掌握:
不是一個懷舊的人,沉溺在過去好無聊
張楚把這次的巡演定名為“微小相見”,取自新歌《到達》中的一句歌詞,對此他給出的解釋是“生活還是很具體的,有時候完全從傳統的大精神概念彼此理解,還是會出現偏差,環境一直在變化,所以我希望用細節細小的東西重新展開”。
現在的張楚租住在北京東北六環,一個和畫家共同棲居的獨立小院子裡,因為靠近機場,經常能聽到飛機掠過的聲音。張楚就在這個偏遠的遠離鬧市區的地方完成自己的新作品,他自己當制作人,然后請《造飛機的工廠》時期的混音師來完成后期混音。
其實在2014年,張楚就數字發行過自己的EP《清楚》,包括把《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重新編曲,但對於闊別已久的張楚新作品,外界的反響比較平淡,沒有再現當年《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加盜版超過50萬張的銷量和影響力。對此張楚說:“平淡就是不激烈,我的音樂不激烈,當時我也沒有出去吆喝,我該怎麼吆喝呢,‘啊我全面回歸了’,是不是頭條就登這些東西,就有關注度了,我怎麼就不習慣這種方法呢。”
去年張楚也上《中國好歌曲2》助陣當年“戰友”趙牧陽,他說時代改變了,世界已經變化太多,“不像年輕的時候喊一句口號就出來了,生活不是有一個個人就決定,有很多不同的組合而成,要完備管理好自己和生活的關系,是需要價值選擇……”然后張楚還笑說:“不得已的時候也可以上綜藝節目推廣新歌。”
除了自己的“微小相見”巡演,張楚還將參加一場“中國搖滾30年”演唱會,對於時下有關搖滾樂的懷舊風潮和各種“情懷”的重拾重現,張楚說自己沒有太懷舊,不是一個懷舊的人,“懷舊就是沉溺在過去,懷舊好無聊”。
張楚一再強調的是:“現在是最錯綜復雜的時代,是價值觀混亂還沒有真正有新的面貌的時代,我的新專輯就是要掌握自己。我們是作為社會化的存在,需要有共鳴,但每個人對個體的需求越來越仔細和真實,這是很健康的事情。”張楚說自己越來越喜歡研究,喜歡細節,“我的音樂被認為似乎代表著對善良的追求,必須讓我健康起來才能成為一個有能力善良的人”。
張楚說
從最近做客《魯豫有約》的畫面,就可以看到張楚越來越干瘦,他自己都笑說去取快遞被工作人員誤認為“吸毒”,但從他接受採訪,以及被很多90后記者盤問的對答情況看,他的狀態還算不錯,思維還是比較跳躍,經常說出帶有哲理的詩一樣的句子,但他強調不喜歡被說是詩人。(以下部分取自《魯豫有約》)
關於當年隱居
“覺得我的文化概念有不完備的地方,對自我和他人的識別是有缺陷的。經過這麼多年,發現人最大能救贖自己的,就是讓自己安靜。”
關於安靜
“經歷了歷史的混亂,經歷了政治的反復,經歷了文化的邊緣和主流,當浪漫和粗俗被否定的時候,我的心會更安靜,會更接近想要的永恆。”
關於愛情
“在愛情上沒有花很多時間去挽回,是付出得太少。不是那麼需要愛情,試了一下,不太靠譜,和周圍的人有點脫節,現在更喜歡一個人待著,沒有一個新的知識促進往那個方向走就特別孤獨。”
關於中國搖滾
“中國的音樂行業是個小行業,人的豐富性和精神性歷練會差一些,不管多有錢多有名,知識結構、腦力、專心度、潛意識都不夠優質。”
關於搖滾精神
“搖滾精神是一種生命的更新,周圍的人還用十幾年前對搖滾樂的理解去做搖滾樂,就不願意接受,這個環境已經很封閉了,再不去嘗試新的有意思的事兒很浪費,還不如不做這個行業。”
關於竇唯何勇
“竇唯要溫和一些,何勇要激烈一些,竇唯對音樂研究的深入是我們這些人最好的,何勇很北京性格,我性格比較內向,喜歡包容的方式看整體,看自己。何勇不是特別能理解,能理解一點點竇唯。”
關於朴樹
“朴樹是更新生的一代,他們的世界觀更明朗,也有個人的小憂愁。我們更熱情,也許這個熱情裡有冷的東西、有堅硬的東西、有個性的東西、有自虐的東西,我們這一代人對社會文化有自我的熱情。”
關於張培仁與賈敏恕
“當年對張培仁的理解有偏差,那個時候大家都年輕,現在看從某個角度除了憤世嫉俗的一面,他們是最願意用人性來放在音樂裡、尊重人性的本質來作為創造力的基點,而不是以偏概全,不是從這一面否定另一面的態度﹔賈敏恕老師從制作東西來說特別嚴謹,北京錄完音再到洛杉磯混音,那個時候在國內都是用簡陋的方式完成,但他就已經開始用國際最正常的工作方式去工作,讓唱片有完備的自己價值理念和審美理念。”(小背景:張培仁和賈敏恕是當年“魔岩三杰”的制作人和老板,對中國搖滾樂的貢獻有爭議。)
關於消費情懷
“消費情懷挺痛苦的,消費情懷是移情,把個人的東西變成一種社會化的東西,如果音樂給人的東西變成這樣一種意義,音樂人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就變成了音樂政治,音樂應該是帶給自己的豐富的自我認識和對世界更多的理解。”(小背景:老狼和汪峰等人在《我是歌手》唱《禮物》,張楚是原唱之一但沒有去,他事后有表態把情懷說成“窮懷”。)
關於苟且
“有的人苟且,有的人不苟且,有的人要解決苟且,有的人認為苟且和別的東西對立,我也遇見過各種各樣的問題,自己人生也碰到過沒有錢的時代,也碰到過很商業的時候,每個人可以做自己的選擇,而且用自己的選擇做出對自己的肯定,才是一個真實的言論,沒有一個言論可以代替所有的人。”(小背景:張楚在自己的微博對高曉鬆和許巍合作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有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