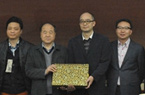原标题:评“乌青体”: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
乌青和他的“废话体”已经成为一个诗学事件。这一事件与当年的“梨花体”、“羊羔体”很类似而又不同,它似乎在让更多的人远离诗,可如果认真想想,它引起的话题却离诗的本质更近。“梨花体”和“羊羔体”只是针对两位诗人的名字,利用谐音的方式而命名的,“废话体”的指向已经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废话”——这两个词定义了人们对口语诗的核心认知。
从乌青的成名作《对白云的赞美》说起:
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
白,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特别白特白
极其白
贼白
简直白死了
啊——
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再读一遍,再读十遍,读者们依然无法读到更多的期望中的“诗意”,它只不过是“对白云的赞美”。既然如此,这首诗为什么在许多诗人、批评家眼里是重要的呢?
从文本上看,整首诗都在感慨“天上的白云”的白;如果再敏感一点,可能会发现诗句中对“白”的表达具有一种递进关系,但这显然不足以说明它是“好的”和“重要的”。在基本语义上,这首诗确乎类似于废话,除了表达“白云很白”的慨叹,不负责提供任何其他信息或意义。反对者的核心论点即来源于此:这也叫诗?如果这是诗,我一天能写一千首。然后开始了狂欢式的模仿,这些仿作网上比比皆是,无需印证。
但与普通网友相反,乌青的支持者却大都是专业诗人和作家。比如诗人周亚平说:“因为我的确喜欢乌同学这个小伙子,他不追随唐诗宋词也不追随艾略特,幸运的是他还不‘垮掉’,他把我当年想干的人和事,都干了!”蒋方舟在知乎发表文章支持乌青:“他有其他的野心。他要超越语言。看不懂就看不懂,因为它被写出来,也不是为了被看懂的。”韩东也在微博上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乌青的诗具有先锋性。
综合起来看,双方争论的起点首先是诗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到底什么才是“诗”的问题。和小说、戏剧、散文集中的文体相比,“诗”是最难定义的,因此人们通常从它的反面来理解它,也就是通过“什么不是诗”来映射“什么是诗”,诗通过自己的背反来存在。这一段有点绕口令,但事实确实如此。绕了半天,我想说的是纠缠于诗的概念和界限是毫无意义的,诗不应该封闭自己,读者也没必要只用一个定义来套所有的东西,或者只在自己的只是经验领域来理解所有的作品。
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角力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懂”,读得懂,或读不懂。在这一点上,双方自说自话,各有各的理。但把“懂”作为判断是否是诗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许多读者觉得读不懂,或者认为它毫无意义,是因为这首诗所指认的逻辑起点,正是他们思维中的一个盲点。这首诗起源于日常事物的一次非常态的震惊,具体点说,就是起源于我们对“天上的白云”这一日常事物的震惊。在大部分时间里,白云和所有的自在之物一样,先于我们而存在,我们对它的接受是本然的。但一旦我们去特别观照白云,或者说是“重新发现”白云,并且震惊于它的白,而且我们极其想赞美它,说出它到底有多白——问题来了,困难也来了——面对那么白的白云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它的白已经超出了我们感知和表达的界限,我们该怎么办?通常情况下,当人们不能用直接的叙述语言来描述一种事物的状态时,我们会采取修辞手段——比喻、通感、夸张等等来表达。还是举一个“白”来说,传统相声里形容一匹布非常白时有几句词:“这块本色白,气死头场雪,还不让二场霜,气死了头号的洋白面啊。”
如果借用其他任何白的事物,使用了所有的修辞手段,也无法传达出人们所感知的白云的“白”时,又该怎么办?或者说,面对世界,当所有“有意义”的语言都失效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人的自然反应,回到文学和语言最初发生时的状态:只能不停地感慨式地强调天上的白云真白啊,非常白,极其白,贼白,白死了。正如我们在疼痛时的第一反应是“啊”,而不是其他富含意义的表述。因此,这首诗的第一层重要性就在于,它以诗的方式反映了曾经被人们认为无所不能表达的语言的失效,在极端体验面前,语言并非无所不能,诗也同样如此。
很多读者反驳说:如果这就是诗,那我也会写诗,然后模仿着来一段。但关键点在于,只有乌青第一个意识到并以诗的形式表达的“传统的诗学语言”的失效,所有后来的模仿作品不但没有消解这首诗的价值,反而强化和印证了它的先锋性。正如韩东所言:“别说你可以做到,在乌青是自发效果。”自发与模仿,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境界。如果没有乌青和他的“废话诗”,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自己日常生活里有那么多体验是无法表达的?这首诗确实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处在了类似的位置。意义必须产生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这有点像摄影。摄影的价值在哪儿呢?在于对瞬间的把握。但人们凝视照片时常常忽略一点,就是照片的边界。正是边界的存在,决定着照片的意义空间和可能性,对摄影作品而言,全景图是无意义的。《对白云的赞美》这首诗的作用,就类似于摄影作品的边框,只有它框住了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才会存在,也才会产生意义。
我以为,《对白云的赞美》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韩东写下了《大雁塔》和《我见过大海》,并发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论断;当杨黎高举“废话”的旗帜并实践;当伊沙等诗人执着于构建口语诗的体系,引领了一股潮流,这一脉络总要走到这一步。更何况口语诗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书面化的诗歌语言无力也从来没想过去表达一些日常的经验,但如果一部分日常经验连口语也表达不了,“废话”的出现自然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这首诗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它的出现却生发了意义。当然,在讨论了这首诗的“好”和“重要性”之后,我们也回避不了另一面,就是这类诗的价值不会被模仿之作消解,但它们会因为可复制性以及作者对其价值的过分强调而自己消解自己。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口语诗最大的危险,因为一部分诗人对“口语性”的顽固痴迷与反对者的诗学处于同样的逻辑。好在从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诗总会发展,总会在人们不知觉处生发新的枝叶。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