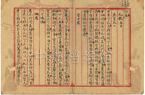■1894年孫中山提出的“振興中華”,成為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先聲
從歷史源流上看,中華民族復興觀念在對中華民族的自我定位上,包含了承認中華民族暫時落伍與重新趕超西方列強兩個向度。這兩種思想元素實際上在甲午中日戰爭前都已形成,前者如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指出中國“船堅炮利不如夷”,后者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通過“師夷長技”趕上西方,“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但由於甲午戰爭前現代民族觀念、中華民族觀念尚未形成,自然也就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復興觀念。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醞釀,可追溯到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發生后民族危機的加深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甲午戰爭失敗后,中華民族開始有了覺醒意識,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開篇所言:“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的打擊使少數先進的中國人意識到了“不如夷”,但朝野上下依然酣睡於天朝舊夢,大有雨過忘雷之意。被東方“島夷”日本打敗所導致的亡國滅種的危機,使中國面臨“國無日不可以亡”的空前險境,才徹底打破了中央王國、天朝上國的千年舊夢——“天朝夢”。危機同時又是轉機,正是在“天朝夢”坍塌的廢墟上,催生了建設中華、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
革命派領袖孫中山率先號召“振興中華”。他於1894年11月在美國檀香山創建了興中會。興中會成立宣言明確指出:設立本會的目的“專為振興中華”,該口號成了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先聲。他在清末奔走革命的過程中,多次闡釋了實現民族復興、趕超西方列強的思想。例如,他在1905年的《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中指出:中國通過學習西方,可實現超常規發展,不僅“突駕日本無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他在1906年給外國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國這一“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的復興,將是全人類的福音”。
這一時期,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在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醞釀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01年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1902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最早使用了 “中華民族”的概念。值得重視的是,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還曾使用了“古學復興”“復興時代”等詞,中華民族復興觀念呼之欲出。
從總體來說,近代語境中的民族復興,包括以民族建國為契機恢復民族獨立,以趕超列強為目標恢復民族地位,也包括以“少年中國”號召恢復民族活力。梁啟超在1900年發表了《少年中國說》一文,痛陳“老大帝國”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國”重振,堅信“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他寄希望於少年,稱“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民族復興還包括民族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思想在清季也已萌生。1905年10月,鄧實在《國粹學報》發表《古學復興論》,預言“十五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二十世紀則為亞洲古學復興之世”。其所謂“亞洲古學復興”重點即在先秦時期中華元典文化的復興。此時,中華民族復興話語雖未定型,但該觀念所包含的基本義項已比較清晰。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