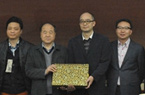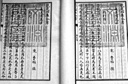文學的鈾質在生活深處,文學的魂魄在人民之中,並由此決定了任何文學創作,都既是對人民生活的藝術化反映,又是對大眾感情的聚焦式凝結。各種內容與形式的文藝作品,從根本上說,都是馭筆於事和動情於衷的精神產物,所以決不能矯揉造作,更不能“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讀玉潔的長篇小說《狗來兒》,首先感到的,是它對深切生活體驗的生動描述和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通篇都體現著對人民大眾的深情厚愛。其次,是它在文學架構和藝術布局上的傳承與創新。
《狗來兒》以最朴素的形式訴諸於世的,是最真實的生活和最真摯的感情。其優勢在於不渲染、不矯飾、不做作,按照生活的固有邏輯和人們的心路歷程與情感軌跡,藝術地還原了客觀世界所存在著的心理糾葛和愛恨情仇。而且,作者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對生活的藝術還原上,而是及時地秉持著真、善、美的人性准則,富於張力地對愛恨情仇施以精神裁量與道德評價,並通過合理的藝術回旋,使愛恨情仇實現了具有道德理性的轉移與切換,將人性的詭譎有聲有色地升格為人性的純淨。
顯然,承載和傳達這認識價值和精神寓意的,正是《狗來兒》的人物、情節、意境與題旨。作者在50余萬字的篇幅中,精心建構了一個現實生活的演示台與世俗社會的橫剖面。此中,各色人等的表演雖都具有特色,但又無一例外地代表了一種社會人性的構成與現實生活的趨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各自都既是原型,又是典型。讀者從他們身上,每每都能體悟到人的普遍屬性和社會的倫常演繹。比如主人公狗來兒,他的勤謹、包容、深厚、善良,就幾乎囊括了中國傳統美德的所有構成要素。而在楊海棠、楊文清的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卻顯然是對這種美德的挑舋與悖逆,狡黠、自私的秉性和詐賴的行為中所潛在著的,無疑都是需要予以譴責和鞭撻的精神孽根與道德沉渣。
作者在作品中所設置的這種基本人物關系以及由之所構成的思想情境與藝術格致,其本身就已形成並確証了出現對立和發生沖突的生活質點與人性本能。而事實上作者也正是利用這種對立和沖突,才得以一浪攆著一浪地把情節推向了高潮,並在矛盾對立不斷激化的終點上,出人意料地呈現異乎尋常的破解與轉圜,從而實現“理”的回歸與“善”的折返。
誠然,這是人物塑造和情節設計上的機巧,但更是對人性本質的深層次開掘。任何成功的和有價值、有意義、有效能的文學創作與藝術創造,都隻有臻於這樣的境界和實現這樣的旨歸,才能算是對生活真理和文學真諦的准確理解與有效踐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狗來兒》不但實現了情節的推進、情感的升華,而且創造了一種以真情代替矯情、用真實置換虛假的藝術風格。
當然,在《狗來兒》所帶給我們的新風尚與新氣象中,除了純真、質朴、清新、剛健和情節有致、內容充實、題旨宏闊之外,更有那嫻稔的民族化的敘事方式和親切的鄉土化的語言風格。從濃馥的泥土氣息和飄逸的民族風韻中所沁滲出來的,不僅是一陣陣田野的清香和一縷縷陽光的映照,更是作者對社會責任的自覺承載和對時代使命的勇敢擔當。而這一切所體現和所承載的,則正是對人民性與社會性的深刻發掘與高度濃縮。
由此可見,《狗來兒》的生活化敘事和社會化表意及其對主題、情節、人物、場景的擷獲與熔鑄,都無不鈐刻著時代變革、社會轉型的鮮明印跡。而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實現路徑就是心向人民大眾,投身生活洪流。作者玉潔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基層,有著濃烈的鄉土情結和深切的生活體驗。因此,在這洋洋50余萬言的敘說中,處處都凸顯真心,流露真情,表達著摯愛生活與人民的拳拳之意。而這,既是《狗來兒》的成功之因和創新之源,又是《狗來兒》的精神“質”點與藝術“亮”點。
《 人民日報 》( 2014年12月02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