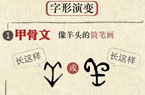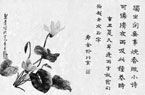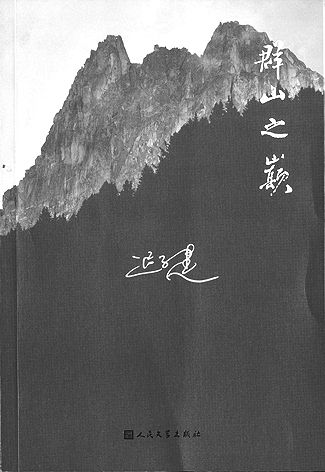
《群山之巔》 遲子建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遲子建的上一部長篇小說《白雪烏鴉》面世時,我還是她作品的出版人,時隔五年不到,她又寫出了新的長篇《群山之巔》,而此時的我已離開了出版的一線崗位。身份的轉變,使得自己的閱讀淡去了功利,歸於寧靜與純粹。
遲子建在作品的“后記”中以一首小詩作為《群山之巔》創作之旅的結束,其中有這樣兩句:“我望見了——那望不見的!”這無疑是一種發現,只是這種發現會如同作品結束時那句蒼涼的“一世界的鵝毛大雪,誰又能聽見誰的呼喚”嗎?我想不會!盡管在滿地“娛樂至上”的聒噪聲中,我依然堅信溫潤、優秀的文學作品會告訴我們許多、許多……
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對長篇小說敘事結構,有著孜孜不懈追求且獲得極大成功的作家。直面“偽滿洲國”那段歷史,作者中規中矩地採用了“編年體”敘述﹔到了“額爾古納河右岸”,一個民族的挽歌在遲子建筆下,竟然以交響樂式的史詩體呈現﹔面對“白雪烏鴉”這樣的情境,作者把哈爾濱大鼠疫真實歷史中的達官於駟興和名醫伍連德的行蹤,筆墨均衡地融入小人物的描寫之中,勾勒出一幅死亡面前眾生平等的生活圖卷﹔登頂“群山之巔”,遲子建直面當下復雜的社會生活,而她的敘事結構更是別出心裁,筆者孤陋寡聞,實在想不出有什麼現成的概念可以用來描述這樣的結構,於是自己臆造出一個“環形鏈式”的詞兒來。所謂“環形”是指整部作品的結構呈環形狀,故事從辛欣來弒母奸女拉開帷幕到他歸案而曲終,而這個環形又好似由節節相扣的鏈條所組成,全書17個小題就是這根鏈條的17個小節,每個小節的結束與下一個小節的開頭相勾連,引出新的人物,牽出新的故事。《群山之巔》中先后登場大大小小的人物多達幾十口,時間跨度也有幾十年,這曲“愛與痛的命運交響曲,罪惡與贖罪的靈魂獨白”,說不上誰是主角誰是配角,每個事件似乎都是核心,但作品凸顯的普通人生命的尊嚴這一主題,恰恰就是通過這一群小人物來完成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內容,我想遲子建才採用了環形鏈式結構,這種設計別具匠心,巧妙機智。依據不同的內容來構筑不同的結構,本應是文學創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但事實上卻並沒有多少作家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而遲子建通過自己的作品告訴了我們:她能!
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在長篇小說寫作中很善於以小搏大的作家。在她的幾部長篇代表作中,時代是大的,時空是大的,事件是大的,雖也有些“大”的人物,但能夠給讀者留下更多記憶、更多想象的則還是那些“小”的人物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偽滿洲國》記錄的那段歷史不可謂不大,兒皇帝溥儀在歷史上留下的聲名也可謂“顯赫”,但在這部洋洋60余萬言的長篇中,躍然紙上更多的則還是那些小人物的群像﹔《額爾古納河右岸》作為第一部通過表現鄂溫克族一個部落的式微,而反思文明進程的長篇,主題當然是沉重而哀婉,但作者偏偏要通過一位年逾九旬的酋長遺孀對自己愛情的溫馨回憶而呈現﹔《白雪烏鴉》以發生在上世紀初哈爾濱的那場大鼠疫為主線,其對當時生活影響之震驚我想不會亞於正在非洲大地上肆虐的“埃博拉”,雖也有達官和名醫串場,但主角依然是一群小人物﹔到了這部《群山之巔》,時間跨越幾十載,而這幾十年恰是當代中國發生劇變的時光,然活躍於這塊巨大時空天屏上的卻無一不是小人物,從辛七雜辛欣來到安雪兒安平、從繡娘單四嫂到李素貞唐眉……他們在流逝的歷史長河中不會留下一絲痕跡,但正是他們撐起了這巍巍的“群山之巔”。
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很善於將生活用文學方式呈現出來的作家。也許有讀者會反詰:這不是廢話嗎?文學和生活什麼時候又割裂得開呢?道理的確如此,但道理卻未必等同於事實。特別是在當下,我們的閱讀實踐中經常會遭遇這樣兩種情景:一是作品中的生活信息並不缺乏,但也僅僅就是生活信息的堆砌或是一個個看得下去看不下去的故事而已,這類作品或許可以叫作不缺信息缺氣息﹔另一種則是作品變成了文學技藝的大秀場,通篇看到的只是蒼白的炫技,其實說模仿更准確,生活信息則稀薄得可憐,這類作品或可稱之為不缺技藝缺生命。而遲子建的作品則一方面是密度不小的生活信息,一方面又是靈巧的文學呈現,《群山之巔》可謂這方面的范本之一。設想一下,如果濾去這部長篇的文學手段,作品中的生活信息該是如何的密集與破碎,而現在經過遲子建的妙手編織,閱讀的感受立即就變成了舒緩與意味。這才是美的文學與美的小說。
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小說寫作的多面手。在中國文壇的小說寫者中,短中長三頭並進者不少,但像遲子建這樣均獲得成功的的確不多。其實專注於一點而成就卓然就很是了得,如同歐·亨利、契訶夫一輩子專注於短篇,也並不妨礙他們成為世界級大作家一樣。我想說的是:對作家而言,重要的是要認清自己獨特的才華稟賦而未必需要四面出擊,能夠像遲子建這樣精通十八般兵器者終究不會太多。
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告訴我們的當然不止於上述四個方面,但僅此四點就已從不同方面對我們的文學研究提出了一個課題:這是一個有著研究價值和值得研究的作家。之所以值得,是因為隱藏在遲子建的文本背后,有值得琢磨,值得望見的東西。面對這樣一位作家,文學研究者實在需要認認真真地從閱讀與體驗做起,而不是從空洞的理念與套路出發。那種缺乏體溫的研究,永遠進入不了優秀文本豐饒的內在世界。
(本文作者系文學評論家、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副總裁 潘凱雄)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