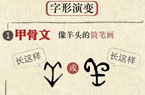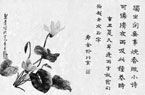《狼圖騰》或許隻能是讓·雅克·阿諾的電影。這位“全世界最會拍動物的導演”絕非浪得虛名。1988年的《熊的故事》,一隻森林小熊的故事感動了無數觀眾﹔2004年《虎兄虎弟》,兩隻老虎的兄弟情同樣溫暖人心。在這兩部電影裡,動物是絕對主角,人類只是陪襯。法國人阿諾用純粹的電影語言找到了人類與動物溝通的方式。
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用特效做老虎不同,電影中的狼全是真的。劇組養了35匹狼,花了三年時間訓練它們,讓它們既保持野性,又能配合拍攝。在片尾字幕上,記錄了每一位狼演員的名字。隻這一點已令人敬服。在如今熱錢涌動的中國電影市場,還有一部電影耐得住性子,以傳統的工藝精神,花六年時間精雕細琢。
影片對狼的神態、動作捕捉得極為生動,無論是狼群在金黃的草原上馳騁捕獵,還是在銀盤般的滿月下長嘯等畫面,都十分優美。導演對狼的群體特征乃至每一匹狼的不同個性都有細致敏銳的觀察。主人公陳陣養大的小狼自是親切可愛,狼王不怒自威的表情更令人不寒而栗。
影片中最大的看點是三場“狼戰”戲,分別是狼馬大戰、狼羊大戰和夜襲羊圈。首先亮相的狼馬大戰尤其令人大開眼界。狼群暴怒瘋狂的報復,人類指揮下的馬群倉皇奔逃,乃至被狼追進結冰的湖中不得脫身,最后活活凍死,畫面令人毛骨悚然,教人感嘆狼的智商、情商之高,竟不亞於人。后面的狼羊大戰、夜襲羊圈盡管也足夠精彩,但視聽奇觀的震撼效果仍稍遜前者。
相較於狼的生動靈性,人物的刻畫就相對潦草了。主人公的個性尚未建立,電影就迫不及待地進入了第一個小高潮。馮紹峰扮演的陳陣單槍匹馬對峙狼群,脫身之后,他說“我被狼迷住了”。死裡逃生之后不是應該怕狼嗎?他過去是怎樣的人,為何對狼情有獨鐘呢?電影沒有交代。竇驍的角色則干脆淪為陪襯。這應該跟導演對中國人、中國上世紀60年代歷史挖掘不夠有關。好在馮紹峰的表演足夠動人,幫助豐滿了人物。
整體來看,影片固然提供了精彩的視聽效果,但對於狼性、人性的探究相對膚淺,遠不能與同樣拍動物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比肩。對有情眾生的珍視和食物鏈的殘酷無情一直是生命的兩難。電影沿襲了小說《狼圖騰》所提出的世界觀——“大命小命”。在草原上,草和草原是大命,其它都是小命,包括人和狼在內。因為黃羊吃草,狼吃黃羊,所以狼是英雄,黃羊才是禍害。這代表了游牧民族的態度,其中潛伏著某種征服者的邏輯。人類與狼爭奪生存空間的“掏狼崽”行為,即使要殺死狼,也始終保持著對它的崇敬。與此同時,影片著力表現人類(尤其是漢人)的無知,虐殺狼群,破壞環境。這組人和動物的對立關系在《熊的故事》和《虎兄虎弟》裡都出現過,但前兩部片的主題比較單純,《狼圖騰》這樣的厚重題材再老調重彈,便失之輕巧了。“因草原狼產生的恐懼和敬畏,就是人們心靈中所崇拜的圖騰。我有種感覺,我推開了通往草原人民精神世界的那扇門。”電影開始沒多久就用這句旁白蓋了頂大帽子,之后的故事卻跟草原人民的精神世界關聯不大,仍舊回到環保這個基本的普世價值觀上來。
相對於李安、王家衛等中國導演對於氣韻、空間的重視,西方導演似乎更加注重戲劇沖突。《狼圖騰》的鏡頭在風景上沒有做過多停留,剪輯節奏很急促,故事講得險象環生。觀眾剛要開始欣賞廣袤的草原風光,不到兩秒就被切回故事線。不知是否也有時長所限的因素,目前的片長是121分鐘,基本已達到國產商業電影的極限。為了凸顯戲劇性,導演還採用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寫表現局部動作,而很少拉開鏡頭表現人/動物與環境的關系。這個特點也讓該片的3D IMAX效果有點吃虧。
誕生於草原的《狼圖騰》,若能以蒙古音樂貫穿始終,《萬馬奔騰》伴著狼馬大戰,該是何等快事,但影片的音樂幾乎是好萊塢大片的一貫腔調,只是偶爾摻入呼麥、長調等音樂形式。詹姆斯·霍納的配樂不能說不出色,只是全球化有余,到底不夠親切。
有人說《狼圖騰》最適合“沖奧”,其實不然。奧斯卡一向青睞的外語片,都是格局小卻立意深的作品,這部影片恰好相反,格局大而立意淺,走的還是商業大片路線。站在商業片的角度,本片已是童叟無欺,分量十足。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