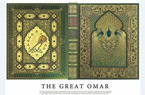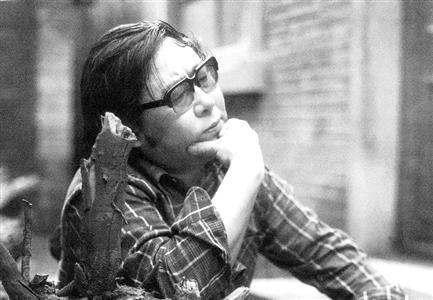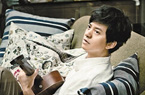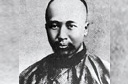早報記者 邢春燕
“我叫蔡瀾,聽起來像菜籃,買菜的籃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蔡瀾在其個人微博簡介上這樣介紹自己,身為美食家,他毫不掩飾對吃的熱愛。然而如果僅以美食家身份去理解蔡瀾,又未免過於狹隘。借著3月26日蔡瀾來滬與粉絲分享美食體驗的機會,早報記者與其面對面,暢聊更全面的蔡瀾。
1941年出生於新加坡的蔡瀾,祖籍廣東潮州,曾留學日本,在香港發展事業,他通曉漢語、英語、粵語、日語和法語。他身上的各種頭銜可謂眼花繚亂:電影制片人、電影監制、美食家、專欄作家、節目主持人、商人。蔡瀾與黃霑、倪匡、金庸並稱“香港四大才子”,才子最厭煩平庸,“任何規定的東西我都不喜歡,我從小就是叛逆的個性,讓我做些平常人要做的東西,我最討厭了。”
40載電影生涯
“好導演要看書”
1957年,蔡瀾得邵逸夫厚愛,擔任了邵氏電影公司的駐日經理,后又被派去韓國、中國台灣等地當監制。40年電影生涯中,他常駐各國,監制了大部分成龍在海外拍的戲。
那40年也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香港電影不僅在東南亞有廣闊的市場,甚至能賣到澳大利亞、非洲和北美洲,而巨大的資金回流又可以給電影制作充實新鮮血液,形成良性循環。然而隨著盜版猖獗,這些市場一個個消失,“以前我說不要怕,翻版要2個小時,等有一天像印鈔票一樣印的時候,就要怕了,”蔡瀾說,“果然這個年代來了,影碟翻版很容易,市場迅速萎縮了,所以香港電影轉而和內地合作,香港特色瀕臨絕望。”
談及目前內地的電影產業,蔡瀾認為雖然市場很大,好導演卻屈指可數。“新導演文字功力很弱,沒有好好看書,”他說,“拍電影一定要看資料,和很多導演聊天,他會說這場戲像美國的一場戲,這個特技像哈利·波特,永遠是二手形象,我們拍電影的時候是從文字變成形象,現在資料多得很,還產生不出一個好的電影,應該怪誰呢?”
蔡瀾目前始終保持驚人的閱讀量,“如果一個寫作人不喜歡看書,他就沒資格做寫作人。”
隻談美食,不談養生
從事電影制作40多年,有一天蔡瀾突然發現,“原來自己不是喜歡制作電影,而是喜歡看電影”,於是他停下手中的工作,開始拿起筆杆子,為報紙寫食評。香港《東方日報》的龍門陣、《明報》的副刊上,皆有蔡瀾的專欄,《壹周刊》創刊后,蔡瀾每周兩篇,一篇雜文,一篇食評。
這種轉變也是基於一次偶然的機會,“爸媽來香港,我帶他們去吃飯,餐廳不僅要排隊,服務也不好,我想我要用文字改變我的人生,”他說,“我不會吃,我會比較,哪一家餐廳更好,不同城市有什麼分別以及國家與國家的一些變化。”
時下中國人最講究養生,身為世界華人健康飲食協會榮譽主席的蔡瀾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最無聊的一條健康意見就是“不吃豬油”,甚至將“健康秘訣七個字,抽煙喝酒不運動”這種反主流的生活方式寫進書中。“時下的東西為什麼要去管呢?任何規定的東西我都不喜歡,做運動我就不喜歡。我從小就是叛逆的個性,讓我做些平常人要做的東西,我最討厭了。”所以大家說養生,蔡瀾就最討厭,“不僅討厭,我一心一意做打破的工作。為什麼好好一個人要和別人一樣呢?為什麼要隨波逐流呢?就算有道理也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
對於年輕人愛用“吃貨”自居,蔡瀾更無法理解。“為什麼要將自己降得這麼低呢?這個社會已經把人降得很低了,不必自己再低了。”他也稱自己並不以美食家自居,而只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人,“簡簡單單,人的生命和想法越簡單越好,簡單隨性是我的人生哲學。”
這種與生俱來的“簡單隨性”也體現在交朋友方面,蔡瀾有一篇“如何識人”的文章近日在微博瘋轉,文中介紹了自己如何根據外貌、氣質和語態去判斷別人的為人。對於朋友,蔡瀾秉持著寧缺毋濫的態度,毫不介意會得罪別人,“如果和我不是一種人,就會回避,因為(和他們交往)這完全是浪費自己的生命。”
《舌尖上的中國》
贏在從食材切入
《舌尖上的中國》火遍中國,蔡瀾是節目總顧問。談及節目成功的原因,他說最重要的是從食材切入,“不講餐廳,不講菜,而講食材是怎麼辛苦得到的,為什麼我們要用這種食材,食材可以怎麼變化,這是很聰明的做法,讓觀眾著迷。”
《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在講述食物本身的同時融入更多人物故事和文化內涵,雖然收視率仍然不俗,網上卻出現了一些質疑的聲音。對此,蔡瀾表示,“講故事可以,但不能太多,最主要的應該以食材為主。”對於第三季,他建議仍然回歸傳統老菜,“中國的飲食文化是拍不完的,應該把一些老菜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留給年輕人,這樣才不會消失。做出來可以讓華人帶出去,影響世界各國的當地人。”
蔡瀾在香港做過多檔美食節目,包括TVB的《蔡瀾嘆名菜》、《蔡瀾品味》,以及美食王牌節目《蔡瀾食尚》等,蔡瀾認為香港和內地的受眾文化截然不同,香港市場小而且更娛樂化,“我的節目是美女相伴,游山玩水,我開創了有美女在旁邊的美食節目先河,而《舌尖上的中國》在香港反應並不激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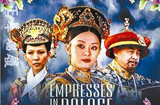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