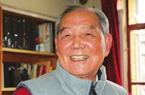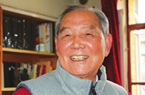青閱讀記者聯系上《丁玲傳》的作者李向東、王增如夫婦的時候,他們正在奔赴烏蘇裡江畔的饒河農場的路途中,那是他們1968年下鄉插隊的地方。像丁玲一樣,他們也對“北大荒”懷有深情,王增如成為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書,正是緣於丁玲1981年回到曾經下放12年的北大荒“探親”,她被臨時調過去接待著名作家。她陪了丁玲、陳明夫婦半個月,去了丁玲曾經待過的普陽農場、湯原農場和寶泉嶺農場等地,之后再無聯系。她沒有想到,丁玲會指名調她回北京做秘書。1982年5月10日,王增如正式到木樨地丁玲的寓所上班。漸漸地,他們夫婦走上了丁玲研究的道路,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版了《無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丁玲年譜長編》、《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丁玲辦〈中國〉》,直到不久前由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備受好評的《丁玲傳》。
離京之前的7月11日,李向東和王增如去看望陳明,他已年近百歲,臥床五年,時而清醒時而糊涂。老人目不轉睛地看著《丁玲傳》的封面和書中的照片,神情激動,眼角漸漸流出淚水。
丁玲已辭世近30年,沒有忘記她的不僅是親人。8月20日至22日,第二屆丁玲研究青年論壇將在寶泉嶺農場召開。李向東和王增如在赴饒河之前,參加了論壇的籌備工作。他們到達目的地后,就《丁玲傳》接受了青閱讀記者的書面採訪。
新材料的發現和取舍
《丁玲傳》於2010年年底動筆,寫了三年。為保証敘述和語言風格的統一,由李向東執筆,而對事件人物的分析,對結構的把握等等,則是夫婦倆一起商量。
這部傳記首先為人稱道的是大量新材料的使用,在書中,它們通常被標記為“據錄音記錄稿”、“據原信”、“據復印件”、“未刊稿”。丁玲晚年的談話錄音是珍貴的一手資料,從未公開,兩位作者把能找到的錄音都整理了,有很多新東西。比如書中使用的丁玲1980年春天的一段錄音,詳細描述了她初到陝北的狀況。還有一段丁玲1983年12月19日跟駱賓基的談話錄音,涉及她與馮雪峰的感情。另一個重要的新材料來源是友人寫給丁玲的大量書信,其中最珍貴的是馮雪峰1946年7月致丁玲的信,署筆名“誠之”。這封信是王增如發現的。2008年前后,巴金書信流入文物市場引起了陳明的警惕,他想把一大批寫給丁玲的信用粉碎機處理掉,因為他沒時間整理,也怕裡面有隱私。幸好這個念頭沒有成為現實,后來王增如夫婦幫忙整理了這批信件,它們也成為《丁玲傳》的有力支撐。
不過,傳記材料總是面臨取舍,這考驗著作者的功力和定力。“寫《丁玲傳》確實有一些材料沒有使用,例如書信中涉及到對第三者的意見和看法,例如寫信人對自己內心深處某種情感的訴說等等,這些東西如果寫出來,肯定會引起獵奇者的興趣,肯定很好看,但這是寫給最信任最親近的朋友看的,寫信人肯定不願公之於眾。”李向東向青閱讀記者申明了材料取舍的幾個原則,“堅持言之有據,堅持不獵奇不炒作的嚴肅態度,堅持保護書信者的隱私。”此外,“還有一些材料,我們覺得雖然比較重要,但與傳記不夠貼切,這些我們將增補到《丁玲年譜長編》的修訂版中,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已經決定出版。”
由於做過《丁玲年譜長編》以及多年的研究,兩位作者對涉及丁玲的史料可以說了如指掌,但他們覺得“堆材料”是不行的,必須從“記錄”走向“思索”,要理解丁玲。為此他們有目的地仔細閱讀了丁玲的全部作品,一是按照她寫作的時間順序讀,二是要弄清她寫每部作品、每篇講話時身處的時代大環境和個人心態的小環境。“這樣就有了新的理解,新的發現,讀出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些看似普普通通的話,其實裡面包含了丁玲的情緒和立場。”李向東說。
站穩立場,平情而論
《丁玲傳》另一個醒目之處是它被學者們普遍贊許的“平實”。傳記作者常犯的毛病,是站在傳主的立場上看問題,或贊美,或辯護。李向東、王增如與丁玲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寫作中的“立場”必然要經受考驗。
對此,李向東說他們得益於清華大學解志熙教授的“指導”。他舉了一個例子,丁玲初上前線,因為是編外人員,會被忘記安排食宿,“最初我們覺得這是不尊重知識分子,但解老師說,當時部隊行軍打仗,忽然來了個作家,還是女的,又不會打仗,這不是給部隊添麻煩嗎?誰知道作家是干什麼的?我們覺得解老師的分析很有道理,站在紅軍的立場的確如此。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站在高於傳主的立場,才能更客觀地看問題。”
說到“平情而論”,更不易處理的是丁玲一生中的“恩怨”(典型的如她和周揚、沈從文),歷來不乏研究者由此入手理解問題,區別只是站在哪一方。李向東不否認這些恩怨裡有個人意氣用事的成分,“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就把問題簡單化了,把恩怨的雙方簡單化了,也把他們看低了。我們想探究雙方當事人‘為什麼會這樣’,他們內在的心理邏輯是什麼。這就要考察他們彼時彼地的處境和心態,為此我們做了一些分析和挖掘。”確實,書中這類設身處地的分析比比皆是,其實在兩位作者看來,沒完沒了地計較恩怨沒多大意思,做研究應該有更廣闊的視角,“但是今天的讀者仍然非常熱衷於這些恩怨,所以必須給予合理的解釋。”
硬氣的老太太
王增如與丁玲有過較多的日常接觸,在她的印象中,丁玲是個“很大氣”、“很有魅力”的老太太,愛聊天,不計較,沒有金錢觀念。王增如說她一上班就被分配了兩件工作,一是處理來信,一是每月替丁玲領工資並支付家中各項開支,“她手中從來不拿錢”。王增如還記得,1985年丁玲請一位青年發明家來做客,聽說他經常省下伙食費買資料,立刻讓她給對方200元買營養品(丁玲每月工資341元)。
王增如從丁玲那裡聽了不少故事。陪她去馬路對面的燕京飯店理發,陪她去復興醫院,一路走一路聊。“這時候,丁玲就像一位會講故事的慈祥老奶奶,用帶點湖南味的普通話娓娓道來,我聽得津津有味。但有時她也會莫名其妙地發脾氣,有一次我忍不住問她為什麼發脾氣,她說:我文章寫不出,思路總不順!”
王增如見証了丁玲的80年代。復歸的丁玲起初風光無限,隨后就因“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一些文藝問題上的立場,站在了主流思潮對面。“她在80年代被說成‘左’,遭受的攻擊幾乎是所有作家中最猛烈的,連一些熟人都對她避之唯恐不及。”那時王增如很為她擔憂。《丁玲傳》裡寫了一個細節,第四次作代會在京西賓館召開,作協理事會選舉,丁玲的得票數大幅下降,有人幸災樂禍。王增如攙著丁玲往外走,心情沉重,丁玲卻非常平靜,說“眼睛不要光盯著京西賓館的紅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現在這點小事算什麼,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麼……”
“丁老當時一點也不害怕,也不氣憤,也不沮喪,那種大氣,那種胸懷,至今想起來我都非常嘆服。”王增如說,“久經滄海難為水啊。我從沒見她灰心喪氣過,她喜歡養的一種花就叫‘死不了’。1984年10月她籌辦《中國》雜志遇到很多困難,有人形容是‘騎虎難下’,她在武漢大學的萬人大會上講演時宣布:那我就‘騎虎不下了’!”
丁玲的魅力
1986年3月4日,丁玲病逝,王增如陪伴她到最后時刻。一個多月前的農歷除夕,丁玲對前來探病的家人說,“你們大家高興吧,我肯定能成佛。”
記者不能確定,與20世紀革命相始終的丁玲留下的這句話到底有何含義,但“涅槃”二字或許正可以獻給這位歷盡光榮與磨難的女性。如今,一部厚重的《丁玲傳》又把理解丁玲和20世紀的新視野放在了我們面前。
李向東說:“丁玲在文學與革命兩個領域,始終走在時代的前面。雖然幾起幾落,但始終不改初衷,‘飛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這句話真是有遠見,丁玲還沒有登上文壇,他就預見到她的一生。我們覺得這八個字是對丁玲最形象、最准確的概括。追求理想,至死不渝,這就是丁玲的魅力所在。今天的年輕人失去了對於丁玲的興趣,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對於理想的追求。所以在今天,了解丁玲,理解丁玲,討論丁玲,我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本版採寫/本報記者 尚曉嵐
(訪談原文將刊發於青閱讀微信:qyuedu)
隻有二十世紀才有這樣精彩絕倫的生命
受訪人:賀桂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主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思想與文化。
《丁玲傳》前所未有地清晰,而且寫活了丁玲
青閱讀:請您對《丁玲傳》略作評價。與之前其他版本的傳記相比,它有何新意?
賀桂梅:李向東、王增如夫婦的《丁玲傳》稱得上史料最全、最有深度。把丁玲生平許多曖昧不清的地方搞清楚了,是這部傳記最重要的一個功德,在我看來它具有迄今所有傳記包括我們的研究都沒有達到的清晰。而且它是這麼深入丁玲的內心,讀完就覺得丁玲好像站在你面前一樣。
新史料是這部傳記最有價值的部分。還有就是作者全面地反復地閱讀了丁玲的作品,體會很深刻。這部傳記的一個特點就是用丁玲的生平來闡釋丁玲的作品。
青閱讀:所謂“知人論世”,從人物生平去解釋作品不是一種很常見、很古老的研究方式嗎?
賀桂梅:但是“知人論世”,一個是要寫作者有閱歷,有見解,能夠讀懂。這和寫作者的能力有很大關系。李向東和王增如是很有見識的人,腦子裡的偏見和框架很少。另一個是要把人之常情帶進去,我覺得他們能夠細膩地體認丁玲和其他人的關系,這個一般的傳記作者很難做到。
他們是想要從丁玲自己的邏輯裡面來解釋丁玲。他們並沒有假裝說我比丁玲高,我要來評價。一個事情發生了,他們用各種材料來解釋丁玲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就是所謂“同情的理解”吧。所以丁玲自己的邏輯,她的思維方式、情感趨向能夠表現出來,這也是傳記寫活了她的一個原因。作者真的是非常理解丁玲的性格,還用一些文學性的細節把她展示出來了,所以書的可讀性也挺強的。我是因為這本傳記而重新理解丁玲。我覺得那些老人們,像李納、賀敬之說寫得“像丁玲”,應該不是一個虛的話。
不過,我一方面贊賞他們從人來論作品,但也覺得有些地方是受到了局限。比如書中解釋延安時期丁玲的創作,就過度地貼了丁玲的經歷。完全用丁玲的經歷是解釋不了某些作品的,那些比較虛構的、文學想象的部分,可能就涉入得不夠深。
丁玲意味著另外一種文學
青閱讀:20世紀的中國女作家,現在經常被提起、被閱讀的是張愛玲和蕭紅。您認為丁玲的作品對於普通讀者依然有閱讀價值嗎?您怎樣看待她在文學上的成就?
賀桂梅:如果純粹作為文學家,隻以作品而論,真的應該說丁玲是比不上蕭紅和張愛玲的,因為她好多作品其實沒有完成,而且她不斷地在變。但丁玲僅僅是個文學家嗎?我認為丁玲這個人,她所帶動的歷史大於她的文學。
另外,我們現在讀張愛玲、蕭紅覺得很順,這與她們的作品和時代疏離的品質是連在一起的,就是說文學純粹是一種個人式的觀察思考,它背后是一個挺中產階級的主體。但是丁玲不同。這還得分開說。她早期的《夢珂》、《莎菲女士日記》,我覺得是一種現代主義的極致,她把人的情感表達得驚世駭俗,在當時是一種非常摩登的姿態。當丁玲向左轉之后,特別是到了延安后,她在文學和實踐,或者說是關起門來寫作還是做革命工作之間做出了選擇。
丁玲不僅是作家,同時是革命者,后來還是共產黨高官。這使她和僅僅作為作家的蕭紅、張愛玲是有差別的。而丁玲對待文學的這個狀態其實是更“20世紀”的。20世紀知識分子一直緊密糾纏著一個問題,要文學還是要革命?要文學還是要政治?現在這個結已經解開了,你天天坐家裡寫也沒人管你,但那個時代你坐在家裡寫,內心是要不安的。所以要理解丁玲的獨特性,她是一個參與性、實踐性很強的文學家。
1931年的《水》是丁玲“向左轉”的標志,小說寫一場大水災,寫難民。夏志清就嘲笑說,這裡面沒有一個人物的面目是清楚的,隻聽到A怎麼說,B怎麼說。但丁玲等左翼作家不是在表現自我,而是在探索如何寫他人的生活,這個“他人”是弱者,是底層,是工農,是勞動者。
到了延安時期,丁玲寫得最好的,是能把她個人的情調趣味和他人的底層的生活結合起來的作品,最好的是《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還寫過《夜》,寫共產黨的男性干部,用意識流來寫他一晚上的生活,他的性意識——那時候別人絕不會寫這個。
丁玲一直想把她個人的很強的情調趣味,她習慣的寫法,和她要表達的工農大眾做一個銜接。總之,怎樣看待丁玲作品的閱讀價值,背后還是涉及到你怎麼理解20世紀。丁玲意味著另外一種文學,是參與性的,同時她身上又有那些現代主義的品質,有她的個性。她的作品是一種“大文學”。
丁玲為什麼被遺忘?
青閱讀:張愛玲、蕭紅現在已成“傳奇”,成了“民國奇女子”,相比而言丁玲較少被講述。在您看來,丁玲在多大程度上被大眾和知識界遺忘了?為什麼會被遺忘?
賀桂梅:“張愛玲熱”由來已久,90年代就開始﹔蕭紅熱起來可能是最近幾年,和電影《黃金時代》有關,不過要論作品的普及,丁玲還是比不上。
丁玲為什麼被遺忘?背后主要是80年代開端、到90年代發展到極致的“重寫文學史”思潮,要告別革命。這也是把左翼作家排除出去,發現左翼之外的作家的一個過程。張愛玲、蕭紅是革命外面的人,當然就被喜歡了。而丁玲的問題在於,她和革命糾纏不清,在革命裡面,又在革命外面。
丁玲被遺忘,其實也有一個過程。80年代一開始熱的是丁玲這樣的作家,認為她是革命體制裡的異端,重視她延安時期的作品。到80年代后期,張愛玲熱興起,告別革命退得更徹底,從找異端走到了到革命體制外面去找,找到的就是張愛玲、蕭紅等等。而張愛玲更是后冷戰時代的象征,她的熱是從港台、美國漢學界開始,是從大陸之外熱到裡面來的。等到了90年代,在大眾社會裡就把丁玲和革命一塊扔掉了。那麼丁玲的被遺忘,就是一種社會心態,一種時代情感或者說價值認同的象征吧。
不過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丁玲還是比較受關注的,不是最熱的,但一直持續著,即便被冷落,還是有人在研究。因為就算你討厭革命,她身上女性的層面還是可以帶進很多批判性的東西。在文學史的評價上,丁玲通常被定位於革命體制內部的異類,而不怎麼重視她和革命共生的、統一的關系。
青閱讀:其實要說人生的傳奇性,丁玲比起張愛玲、蕭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大眾文化裡面,丁玲並沒有獲得她們那樣的影響力。
賀桂梅:張愛玲熱,《黃金時代》熱,背后其實是民國熱。不僅是大眾文化,也包括學術界,涉及歷史、意識形態等等。張愛玲和蕭紅是民國時尚文化的象征。人們關心張愛玲日常生活的情調和趣味,一些很中產階級的東西。人們關心蕭紅,一方面是她作為革命之外的“純文學”作家的象征,另一方面是關心她的男女糾葛。
其實丁玲在民國時期的名聲絲毫不下於她們倆,甚至更火。1934年,最流行的時尚雜志《良友》選出“十大標准女性”,丁玲因她的“文學天才”而排在第一位。但復雜的地方是,丁玲不僅在民國風光,她在延安也風光,五十年代也風光過,之后她成了右派、反黨分子,然后新時期她又回來了,成了“老左派”。
丁玲的身份是多重的,特別是她的后半生,跟共產黨中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而且,她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要是像沈從文那樣就比較好描述,而丁玲是作為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深深地參與到國家建構的過程中。總之,丁玲太復雜,不是一張面孔可以說清楚的。你要是夸她民國范兒,那你怎麼說那個健碩的新中國的高級官員呢?怎麼說那個80年代的“老左派”呢?
丁玲的女性立場是最徹底的
青閱讀:於是網絡上最常見的,就變成了丁玲的婚戀故事,對她和領導人關系的猜測等等。請您談談作為女性的丁玲。她顯然有鮮明的女性立場。
賀桂梅:丁玲在文學創作上最大的突破,或者說她不同於張愛玲、蕭紅的地方,就是她的女性立場。她毫不隱晦,不管她愛什麼人,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都是一樣的愛。在所有的現代作家裡,丁玲寫女性之間細膩敏感而又微妙復雜的關系,是寫得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大膽的——但我覺得不能簡單地說是同性戀。她在性別立場上的徹底,蕭紅和張愛玲都達不到。
青閱讀:丁玲很強勢、很女權嗎?
賀桂梅:丁玲的女性立場,不是西方式的女性主義,也不是官方的婦女解放。到底是什麼呢?我隻能說是丁玲特色的女性主體。丁玲的性別立場有很強烈的主體性,她從來不把自己放在一個弱勢的位置。我們總是替蕭紅惋惜,她身上的悲觀氣質和女性弱者的宿命意識是深入骨髓的。但這樣的東西在丁玲身上一點都沒有,她非常的健朗,是一個明朗干淨的主體。她沒有弱女子的意識和矯情。
塑造丁玲基本的性別態度的,是無政府主義。她很早就接觸到共產主義,但直到1932年才入黨。當時中國知識青年中很重要的思潮是無政府主義,宣揚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什麼男女差別,要打破家庭,打破政黨,打破國家,自己來承擔自己的生活。無政府主義的婚姻觀、性別觀很內在地塑造了丁玲。她是一個絕對獨立的個人,不要依附任何東西。丁玲和胡也頻同居之初,沒有性生活,那就是無政府主義青年的生活方式。
丁玲后來也有婚姻家庭,但是她絕沒有回到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的婚姻關系裡,她在家庭裡絕對是主導者。她沒有弱女子的姿態,這和無政府主義有關,你也可以叫它五四的氣質。丁玲代表著五四時期最最激進的姿態,貫徹到她的性格,她對婚姻的態度,她主宰自己的生活。
丁玲是“革命信念的化身”
青閱讀:您在為《丁玲傳》寫的書評裡提到1979年發表的《杜晚香》,丁玲寫了一個模范共產黨員,這在那個“傷痕文學”風行的年代十分特別。您認為丁玲通過《杜晚香》超越了“受難史”的邏輯,最終完成了一個革命者的形象,她是“革命信念的化身”。但是,丁玲對革命的忠誠是否也使她缺乏對歷史的反思能力?
賀桂梅:如果我們僅僅從生命哲學的層面來解釋,很多年輕時極端激進的人,到了中年或晚年,會回到某種“新古典”。那時更需要的是實踐,是承受生活的壓力,是通過承受壓力來完成自己。杜晚香能用行動來改變周圍的世界,而莎菲就是糾纏在頹廢的心理狀態中。丁玲從早年的“莎菲”走到晚年的“杜晚香”,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完成。
我很重視《杜晚香》,原來普遍認為它是一個宣傳作品,但我覺得不是。小說裡有意識地寫到,杜晚香做報告,不肯用別人給她草擬的稿子,她要說自己的話。這個情節是有象征性的,丁玲是要說,我不是體制的傳聲筒,我是用我的方式來表達我的生命。當然這隻有在今天拉開距離后才看得清。
我覺得革命對於丁玲真的是一種信念式的東西。她不是投機主義者,也不完全是現實主義者,不會說革命出了很多問題,就拋棄革命。這屬於丁玲的個人品質。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丁玲在革命體制裡的位置。她是一個高級官員,親身參與政權的建構,所以她觀察問題的視野、方法和角度其實和一般的“受害者”不太一樣。
革命作為信念,最重要的是它最終形成了一批人,就是丁玲那一代革命者。他們相信人的力量,相信可以創造一個新世界。他們對弱勢,對底層,對工農有一種天然的同情心,而且他們有實踐能力。我認為丁玲達到了這樣的“信念化身”的境界,但是她缺少理論的反思能力,她畢竟是個作家。此外,丁玲80年代寫的東西,也需要重新去解讀,我們對她后期的東西研究得不夠,過分地輕視。
青閱讀: 80年代的丁玲,除了“不合時宜”的作品,還是一個“老左派”,與時代思潮不合,很多人都不喜歡她。這該怎麼理解呢?
賀桂梅:關鍵是,為什麼丁玲在80年代變成了一個“老左派”?今天談這個問題,不是為了分辨當時到底是左派好還是右派好,而是到底怎麼看七八十年代中國的轉型——從革命轉向改革。對此目前還沒有形成普遍的社會共識,但是在學界會越來越明確,就是80年代的變革,斷裂性太強。
我想丁玲的意義就在於,她強調在革命體制連續性的基礎上來講變。丁玲並不是不變的,不要看名號,要看她到底在做什麼。她辦《中國》雜志,有意思的是,她所希望的體制的連續性,體現在對作家群的組織上。丁玲重視老作家、她的同齡人,還有50年代培養出來的作家。她希望以毛澤東時代培養的作家為中堅,上下來帶老作家和青年作家。《中國》也發表遇羅錦、北島、顧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丁玲一點都不拒絕現代派,她是想保持革命話語一定的連續性。但是80年代整個的心態就是一切都要打破。
青閱讀:您認為今天來討論丁玲有什麼意義?
賀桂梅:第一是丁玲自身的豐富性。她非常的博大、強韌,又那麼敏感和細膩,她是性情中人,又干練,能做事,懂人情世故,但又一點不世故。隻有20世紀才有這樣精彩絕倫的生命,所以我稱之為“生命哲學”。第二是深入丁玲,可以矯正我們對中國革命漫畫式的、黑白分明、二元對立的簡單理解。第三個意義在於,可以用丁玲作為媒介,去理解20世紀的中國歷史。在20世紀作家裡,丁玲是唯一和革命相始終的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80年代,貫穿始終,而且她一直處在革命的中心,是每個時期重要事件的弄潮兒,她最能夠代表革命的20世紀歷史的特質。如今,應該可以客觀公正、心平氣和地來看待20世紀的中國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以及知識分子在這個歷史裡面復雜的體驗。
採寫/本報記者 尚曉嵐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