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河》是蔡駿的第21部作品,也是他的第18部長篇小說。在日前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蔡駿坦言,創作過程有如“渡過生死河般艱難”,並借此向日本“社會派”懸疑大師鬆本清張致敬。
這部新作時間跨度三十年,由一起發生在校園裡的謀殺案,引發了主人公穿越前世今生的愛恨情仇。與以往的作品相比,《生死河》的驚悚口味暗淡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大時代”式的敘事手法。出版方磨鐵圖書創始人沈浩波稱:“蔡駿正在擺脫類型文學,開始轉向真正的文學寫作,我看到了他的野心。”
蔡駿自2000年起開始創作懸疑小說,同年因短篇小說《綁架》獲得“人民文學·貝塔斯曼杯新秀獎”。2001年,發表了中文互聯網第一部懸恐小說《病毒》。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他陸續創作了十八部長篇和三部中短篇,累計銷量達到900萬冊,連續9年保持著中國原創懸疑小說的暢銷紀錄。他的早期作品多以驚悚、恐怖、靈異題材為主,從2007年的“天地人”三部曲(《天機》、《地獄變》、《人間》)開始,到去年的《謀殺似水年華》,他的創作風格逐漸轉向對社會問題的深層探討。蔡駿稱,他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最佳狀態,《生死河》是“站在人生分水嶺上的作品”。
開頭類似於《紅與黑》,后面就變成《基督山伯爵》了
青閱讀:有讀者感覺,這部新作沒有以往的作品驚悚,不太像懸疑小說?
蔡駿:《生死河》可以說完全不考慮驚悚了,就是寫了一個人的命運,社會的殘忍和人性的真實。我傾向於這種寫實化的描寫,此風格在日本被稱為“社會派”懸疑,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相對於“本格派”的推理小說,“社會派”不追逐詭計和智力游戲,而是關注社會心理和人性情感,探究犯罪動因和根源。它所傳達出的是一種接近於嚴肅文學的力量,可以讓每個人產生共鳴。《生死河》裡,懸疑只是一種敘事方法,最重要的還是在故事本身。其實。這部書也可以看作是愛情小說。
青閱讀:驚悚和寫實不能兼而有之嗎?這樣讀起來可能會比較過癮。
蔡駿:在處理上不太能夠兼顧,敘事方法上不一樣,隻能有所取舍。故事好看與否首先取決於創意,敘事技巧也很重要。《生死河》的結構很特殊,是一個人的兩輩子。開頭類似於《紅與黑》,后面就變成《基督山伯爵》了。編輯說這是我蟄伏五年的作品,其實真正寫作僅用了七八個月,其他很多時間都是用來調整敘事結構,比如開始我用第一人稱寫,后來全部改為第三人稱,從別人的眼光看待整件事。所以,讀到最后你會發現,也許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性。
當下的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期,有太豐富的題材可以關注
青閱讀:作為一名懸疑作家,關注社會問題的角度有什麼不同嗎?會不會直接在作品中引用社會新聞,比如“藍可兒”這樣的事件,應該是不錯的懸疑素材吧?
蔡駿:當下的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期,對於作家來說是十分幸運的,有太豐富的題材可以關注。像莫言通過魔幻手法反映社會,我就是直接去寫社會。比如,《生死河》裡的師生之戀,同學互疑、同事相輕、親情依賴等都是社會關系的縮影。“藍可兒”比較個案,我所關注的社會事件應該是集體性的,比如人做壞事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這樣做。
青閱讀:如果和日本的推理小說相比較,我們的差距在哪裡?
蔡駿:首先是時間,其次是認識。中國人認為推理就是通過邏輯思維來解決問題。日本的推理小說概念很大,奇幻、科幻題材都被涵蓋在內。“社會派”懸疑小說在日本發展了五十多年,讀者、作者、主流媒體等都有共同的認可,像鬆本清張、水上勉、東野圭吾等作家的風格都廣為人知。我發表第一個長篇《病毒》的時候,都不知道懸疑小說是什麼。盡管十多年來的讀者越來越多,但是仍然存在社會偏見和誤解,比如,懸疑小說就是鬼故事,沒有文學性,甚至覺得就是低俗地攤讀物。但是,世界上的一些懸疑小說已經發展到了可以進入文學殿堂的地步,比如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贖》,鬆本清張的《砂器》。我希望,我們的懸疑文學有一天也出現這樣的作品。
青閱讀:你說《生死河》是你人生分水嶺上的作品,是否意味著你已經確定了未來的寫作方向了?
蔡駿:是的,《生死河》和以往的作品區別很大,開啟了新的一頁,我自己也感覺和這部作品共同成長。近幾年,我要專注於“社會派”的寫作。這條路當然不好走,但好像《東邪西毒》裡的一句話:雖然山的那邊還是山,但我還是要爬過去。採寫/本報記者 王茜
(來源:北京青年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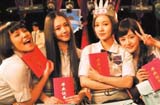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