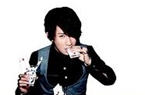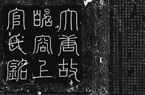在連續取消了中國7地的巡演計劃后,百老匯音樂劇《芝加哥》原定於1月28日至2月1日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的演出也於前天正式宣告“泡湯”。對於這次事故,主辦方給出的理由是“美國制作公司與版權公司就制作無法達成一致”,而后又發生了演員團隊打道回府等風波,主辦方奔赴美國進行磋商未果,而剩下的就是被“閃了一道”的演出合作方和觀眾。
近年,國內多地都在以爆棚的熱情擁抱音樂劇這一舶來品,而已經開票的音樂劇又臨時取消演出這類的事故屢有發生。音樂劇在全球有兩大演出中心:英國的倫敦西區、美國的百老匯。這兩個地方也是國內從業者與愛好者緊盯的兩大標杆。“我們”和“他們”的對接哪裡出了問題?這一“外來物種”該如何在本土落地、嫁接,這,是一個大問題。
今天在本版發表意見的兩位,恰好與這兩大體系淵源頗深,又因為他們都有實操的經驗,其心得或可給我們啟發。
錢世錦,2002年任上海大劇院副總經理時,他和他帶領的團隊第一次將原汁原味的原版音樂劇引入中國,當時業內人士稱他為“老法師”,是對他見多識廣、人脈豐富的行家的尊稱。前年他70歲時被聘為上海大劇院顧問,今年被聘為上海戲劇學院的客座教授,主講“劇院管理務實”,並參與上戲音樂劇中心的工作。
北青報:最近,音樂劇《芝加哥》來華巡演出現了停演事件,雙方好像對裝台、轉場等問題存在爭議,對於這一事件,您怎麼看?
錢世錦:這件事我不願意多講,簡單而言就是一些很不專業的人在從事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怎麼能做好呢?我不願意批評他們,就讓他們在游泳中學游泳吧,算是交了學費,吸取個教訓。
我聽說在合同中有提到一天裝台、一天轉場,這在操作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見這個演出很無序,有人以為現在音樂劇的市場好了,可以賺錢就要撈一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還是要冷靜下來反思下問題所在。
北青報:您剛才提到音樂劇的引進是個非常專業的事情,上海大劇院在2002年將音樂劇《悲慘世界》搬上了中國舞台,是第一部在中國上演的原汁原味的西方音樂劇。但事實上,您是從1988年就產生了引入音樂劇想法的,西方音樂劇的引進為何這麼難呢?談判難點在哪兒?
錢世錦:1988年,我任上海交響樂團的總經理,到美國去考察時第一次看了音樂劇《悲慘世界》,我看過以后感到很震撼。萌生了引進音樂劇的念頭。
1997年,我到悉尼與外方談合作遇到了第一個難題:運輸。對方要求用一架波音747的航空貨運飛機,實現劇團在36小時內從A地到B地門對門專場。當然這個問題后來解決了。
后來又遇到了付款方式、保証金、仲裁等問題,都與外方經過了反復溝通。
北青報:《悲慘世界》2002年到上海以后,外方對演出的場地條件、技術等方面還滿意嗎?在演出中遇到一些周折嗎?
錢世錦:其實音樂劇對演出場地的要求並不高,因為是外方自己布置舞台,對方希望你把一個空劇場拿出來,隻要舞台大小、吊杆等劇場的基本條件具備就可以,其他的舞美器材、道具等都是他們自帶的。
但《悲慘世界》的演出也給我們上了一課,就是“音樂劇怎麼做”。外國人對細節的要求非常高,有一整套的流程要求,這是我們之前不懂的。比如說洗衣服。音樂劇一周8場,每個演員要換10多套衣服,以前我們以為拿到洗衣店去洗衣服就好,但外國演員說不可以,因為他們每天要洗。所以上海大劇院就將一個休息室改為了洗衣房,買了大型的工業用洗衣機、烘干機供他們洗衣服用。
再說幕間入場,也就是遲到觀眾在什麼時間入場的問題,他們的要求非常嚴格。音樂劇一般分兩幕,一幕一小時,要等到一幕演完再入場,對遲到觀眾而言不現實,他們就明確要求要在男主角高喊“一個新的冉·阿讓誕生了”時,有一點點時間,那時候可以入場。
還有換衣服的問題,因為音樂劇的演員一般一個人可能演五六個角色,那至少是五六套衣服,這個衣服怎麼能馬上換好,外國人有一套自己的程序,負責換衣服的阿姨從站的位置到如何拿衣服、道具都有很詳細的流程安排。包括后台如何安排、節目的宣傳冊制作、樂隊入場等等細節都是如此,要雙方協商確認才行。
北青報:2005年,上海大劇院上演了百場《歌劇魅影》,非常成功,但引進的談判過程似乎也很艱難,這又是為什麼?
錢世錦: 在《歌劇魅影》引入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問題,這裡涉及一個常識,音樂劇是沒有劇團的,不像我們有上海芭蕾舞團,音樂劇就是一個制作人把這個版權買下來以后來制作,組團演出。我們在與《歌劇魅影》的版權方談協議的時候,對方提出《歌劇魅影》到亞洲來需要重新組建一個演出團,希望參與到亞洲巡演的四家演出承接方可以先期投入組團所需要的排演費和各種開銷,而這些費用會在以后結賬中再扣除。當時涉及的四家是中國台灣、新加坡、韓國和我們,談好先期投入共擔,可后來突然有一家表示無法支付這個先期投入的費用,一度讓談判又陷入僵局,后來由真正好公司出面擔保,反復協商,另外三家分擔墊付了這個費用,才算達成了引進的協議。
北青報:日本的四季劇團現在成為亞洲音樂劇的標杆,在談到它的成功秘訣時有一點就是音樂劇的本土化和長期公演,您認為中國音樂劇未來的發展會借鑒這點嗎?
錢世錦:音樂劇三步走的原則是上海大劇院最早提出的,就是原版引進、本土化和原創。日本的情況是四季劇團不做原版引進的音樂劇,他們隻引進版權,之后由日本演員用日語演出,這樣可以節省成本。這裡有一個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日本人的民族情結很重,他們希望把外國的好東西“日本化”。
而中國,特別是上海人,比較喜歡洋派的東西,這是它的殖民文化背景造成的,如果你做成本土化了,他反而不接受,覺得不是“原汁原味”了。其實音樂劇對演員和角色的契合度要求非常高,如果一個中國演員出演外國音樂劇,被叫做Mary,確實有點兒可笑。在日本進行音樂劇本土化的過程中也遇到類似問題,所以日本做得比較好的是《貓》、《獅子王》這種演員不露臉的劇目。
現在國內的公司也有在做音樂劇本土化的了,比如《媽媽咪呀》、《貓》,但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票價沒有降下來,由於隻引入版權,本土化的音樂劇應該費用更低,而實際上中文版的《貓》的票價比我引入的英文版的《貓》都要高﹔二是要達到讓觀眾能聽懂、不用看字幕的效果,但實際上現在的唱法做不到,觀眾不看字幕還是聽不懂,那既然都要看字幕,何不用英文原版呢?
這也暴露音樂劇本土化過程中的翻譯問題。音樂劇是用英文唱的,英文的發音和唱法都與旋律吻合,但轉換成拼音的四聲唱法,那就吻合不好了,內容就不對了,翻譯沒有經過反復推敲是不行的。日本在做音樂劇翻譯的時候比較細致,要求除了表達原來的意思以外,還一定要把這個翻譯過來的話和原來的旋律吻合,這是很不容易的。
我認為中國音樂劇的本土化做得太匆忙了,其實要做這件事情,先要讓演員拿到劇本唱,同時讓人來聽,要看演員唱得順不順,要了解聽者的感受,然后修改、調整。比如在《貓》裡有一句“Memory……”日文版就保留下來了,因為不好翻譯,我們就翻譯成了“寂靜……”,這個聽起來的表現力就不對了。所以我覺得音樂劇的本土化,翻譯是個非常專業的問題,還是要慢慢來,不能著急。
北青報:您覺得未來5年,中國音樂劇市場的發展方向是什麼?會建立因劇而設的專業化劇場嗎?
錢世錦:我認為現在的中國音樂劇市場才剛剛起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進行音樂劇市場的培育,引進原版也好、中文版也好、原創音樂劇也好,都是市場所需要的,可以並舉發展,能培育好一個音樂劇的市場才是關鍵。這10多年來,我們不斷引進原版音樂劇也是在告訴觀眾什麼是音樂劇,逐漸培養這個觀眾群體,獲得他們的認知度、認可度。
我覺得中國現在還不具備建立因劇而設的專業化劇場的條件,主要是還沒有足夠優秀的作品。在中國原創音樂劇方面,我也經常思考,我們非常需要好的故事,好的劇本。
文/本報記者 陳凱一
(來源:北京青年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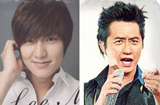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