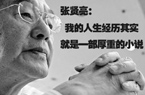何人繪得蕭紅影
“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遭盡冷眼……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1月22日,31歲的蕭紅在香港受盡病痛折磨,臨終時,手書此一句,成為絕筆。這位身世飄零的天才作家不會想到,在她身后70余年間,自己生前的遭盡冷眼,正全然被各階段與她有關的熱情四溢的影視及文學傳記作品所取代——據統計,近年來有關蕭紅的傳記,已經達到70多部。
“實際上,這些有關蕭紅的傳記,包括影視作品,關注點並未集中於蕭紅作品本身,而是更為關注蕭紅復雜的情感和飄泊人生,這樣看起來,於蕭紅還是有些悲哀的。因為蕭紅畢竟是作家。”廣東文學評論家、詩人、學者林賢治,9月27日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這樣表示。
“何人繪得蕭紅影,望斷青天一縷霞。”這是蕭紅的好友聶紺弩先生專為蕭紅所做的詩行。
如何才能還原出一個真實的蕭紅?蕭紅的傳記作者們,通過作品,回答了這個問題。
漂泊者蕭紅的際遇考証
僅從蕭紅短暫但跌宕的人生軌跡來看,她能用來釋放才華的機會,真是少之又少。
蕭紅一生顛沛流離,先后在哈爾濱、上海、日本東京、北京、武漢、西安、重慶、香港等地流亡寫作。蕭紅的一生中出現過五個男人,三次婚戀,兩次失子。
如果從1933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算起,不足9年(另一說為8年)的創作生涯,蕭紅前后共出版過11部集子:《跋涉》、《生死場》、《商市街》、《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蕭紅散文》、《小城三月》、《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創作總字數近百萬,她的人生跟她的作品一樣,風雨飄零,長久寂寞。
也正因如此,蕭紅稍縱即逝如曇花般綻放的人生和才情,成為后來者們唏噓感嘆的描摩對象。
在各版本蕭紅傳中,對蕭紅人生際遇做大量感性描述的作品,當推王小妮《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長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葉君的《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中國社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等。
蕭紅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經過二十余年搜集考証,寫成《跋涉生死場的女人蕭紅》(華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曹革成的《我的嬸嬸蕭紅》(時代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則從家人的角度,對蕭紅生平做了詳細描述。
天才蕭紅的靈性發掘
實際上,關於蕭紅的泛研究,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開始,直至現在,前后跨越70多年。許多人為能寫好蕭紅傳記,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去考証。
蕭紅文字的靈性,俯拾皆是。在《呼蘭河傳》裡,她寫道:“呼蘭河這小城裡面,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在《生死場》中,她慨嘆:“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在《手》裡,她形容女主角的瑟縮:“等楊樹已經長了綠葉,滿院結成了蔭影的時候,王亞明卻漸漸變成了干縮,眼睛的邊緣發著綠色。”
以文立命,是弱女子蕭紅的終生追求。《生死場》,筆觸之細致、動人,完全適合拿來做人類學、社會學、生物學的參考資料﹔短篇小說代表作《馬房之夜》、《橋》,極簡筆法寫盡底層民眾人生寂寞、孤苦和蒼涼。不僅如此,她的散文、書信、詩作,均是天然至透徹。
與蕭紅同時代的張愛玲,情事同樣坎坷,且也很長一段時間沉寂文壇——直到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將其作品再度發掘。也正因此,張愛玲常被人端出來與蕭紅做比較,且認為各具千秋。
但《漂泊者蕭紅》作者林賢治認為,蕭紅的文學成就,超過張愛玲。
就文學創作本身而言,蕭紅的關注點是弱勢者,是弱勢文學。她的筆觸即使是在描摩弱勢人群,但筆下依然有溫暖,有溫度,是從正面看人。“而張愛玲不同,她是從背面看人。張愛玲看到的是陰暗和隱私,冷靜而冷漠。”林賢治說。
“張愛玲是市民社會的寵兒,而蕭紅關注的,是當時社會真正的最底層。”林賢治說,實際上,從現實意義上講,蕭紅的作品更具大格局,大氣象。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是很難得的,因為當時文人的生活層面,基本是遠離底層人民,即使寫下層社會的鄉土小說,也是自上而下的關注,不少左翼作家,在寫到底層、寫到農村生活時,寫得更多的,是階級斗爭。而蕭紅的字裡行間,則異常鮮明地標示,自己正處底層人民中間,是弱勢人群中的一員。
也正因如此,有關蕭紅的傳記,在文理方面研究更為深入的越來越多。這其中的代表作包括著名學者林賢治的《漂泊者蕭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美國葛浩文的《蕭紅評傳》(1979年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1980年在台灣再版﹔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出版),季紅真的《蕭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等。
作家蕭紅的現實悲哀
蕭紅研究界目前所處的一個現狀,不是人們不關注蕭紅,而是,很多時候人們並沒有給她正確的認可。
在文學史上,蕭紅被定位為左翼文學陣營的一員、魯迅的學生,而對蕭紅難得獨到的文學性,欠缺深層次挖掘。在這方面,肖鳳的《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因為評判思想明顯帶著政治眼光,在當下評論界飽受爭議。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茅盾的《呼蘭河傳·序》影響之大,就已經為蕭紅作品定了調,但茅盾所代表的那個時期主流評論的聲音,恰恰遮蔽了蕭紅作品的光焰。
林賢治認為,其實,就連魯迅也不曾讀懂蕭紅,因為,魯迅為《生死場》做序時,曾說小說體現的是“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但,蕭紅的文字裡不僅僅於此。但凡離開了作為女性、作家的自覺,是無法理解蕭紅的。
之后,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整本書,對蕭紅進行了不到一行字的評價,蕭紅在大眾視野裡,僅僅成為一個符號。至此,從主流到非主流文學界,蕭紅文學從未得到認真的研究。
“即使現在這樣熱鬧地推出各種文學傳記、電影紀念蕭紅,可是,要讓讀者或觀眾把目光聚焦在蕭紅作品本身,也很難。”林賢治慨嘆,這對於蕭紅,真是一件可悲之事——寫的是大眾作品,真正欣賞的,反而是小眾。實際上,蕭紅文學作品的影響和被肯定程度遠低於張愛玲,但絕不能因此而否決她在文學上的優秀甚至是偉大。
“文學歷史未必是公正的。”林賢治說,蕭紅是否為學院派所認同,是否為大眾所認同,那很難講,可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寫蕭紅的作家們,都有這樣一個想法,一是安慰自己對於蕭紅文字及人生的迷戀,另外一方面,仿佛冥冥中安慰了蕭紅哭泣的靈魂。
蕭紅雖然生前飽受冷落,但身后,尤其是當下,受到文學界如此矚目,應該略感安慰吧——除卻以上較具代表性的蕭紅傳記,目前,市面上常見的有關蕭紅的文字作品,還包括:王觀泉的《懷念蕭紅》(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鬆鷹和劉慧心的《落紅蕭蕭》(四川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華的《呼蘭學人說蕭紅》(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秋石的《蕭紅與蕭軍》(學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丁言昭的《蕭紅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等。
□文/本報記者蔡俊
(來源:烏魯木齊晚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