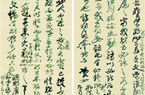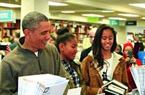江蘇出土的西周雞蛋
說起考古發現,人們更習慣和遺址、墓葬,乃至石器、青銅器、陶器、瓷器這些生硬的器物聯系在一起。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王仁湘研究員告訴沈陽晚報、沈陽網記者,考古發現,其實也發現了為數眾多的食物遺存。他說:“有的發現非常重要,它們改寫了我們已知的食物史。”
沈陽法庫的兩斤遼代古酒
中國的飲食文化源遠流長,地處東北的遼寧自然躋身其中,多年來的考古發現証明了這一點。現在,人們都習慣了吃大米,小米雖然已經成為小眾食品,但是人們習慣上還是認為,小米是營養價值高的食品。
大家都知道,黍和粟,統稱為小米。事實上,至少在5000多年前,甚至更早,小米已經成為了遼寧人的主食。在沈陽新樂遺址,出土了距今約5000年左右的碳化黍粒﹔赤峰蜘蛛山也發現了屬於新石器時代的粟粒。
1955年,遼陽北郊三道壕西漢農村遺址,出土了碳化的高粱,據說這種名為赤粱的高粱,放在酒中可以讓酒變紅。屬於漢晉時代的朝陽袁台子柳城遺址出土了碳化谷子及儲存谷子的三座圓形糧倉,根據糧倉容積,可以儲存谷子約十五萬斤。從規模上看,應該是政府的糧庫。
但最神奇的,是在沈陽法庫葉茂台7號遼墓出土的兩壺酒。
曾經親歷7號墓發掘工作的著名考古專家馮永謙告訴記者,在7號墓中的一張木桌底下,發現了兩件白瓷壺,其中一件中竟然有液體,當時為了確定液體是什麼,馮永謙還喝了一口。
“那個酒顏色是一種特別淡的黃色,很清澈,聞起來沒有什麼味。喝起來,也沒有什麼味。”馮永謙說。
“當時沒擔心這酒有什麼問題嗎?”記者問。
“當時也沒想那麼多啊!”馮永謙笑言。
瓷壺中的液體很快被送去化驗,結果出來了,清楚地標明液體中含有微量乙醇。這個無疑証明,壺中的液體就是酒!馮永謙說:“應該是糧食酒,而且考慮當時遼寧地區的農作物,高粱酒的可能性比較大。”
馮永謙告訴記者,當時壺裡的酒差不多有2斤,而今,這2斤遼代高粱酒就存放在遼寧省博物館內。他說:“現在還有多少不好說,但肯定有!”
在法庫的遼墓中出土千年古酒,此前未曾有過,在考古史上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發現。
4000年前的一碗葷面
遼寧雖然不乏食物出土,但是因為食物遺存並不容易被保存下來,所以我們能看到的色香味有限。近年來,西北地區在考古發掘中多有好玩的食物被發現,這與當地干燥的氣候條件息息相關。
2002年,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出土一碗距今4000年的古老面條。此前的常識,中國古代的面條本來隻有2000歲上下的年齡,它怎麼一下子古老了這麼多呢?
王仁湘介紹說:“在喇家遺址20號房址內的地面清理時,在一個陶碗裡發現一堆遺物。它的下面是泥土,而碗底部位卻保存有很清晰的面條狀結構。這些條狀的物件粗細均勻,卷曲纏繞在一起,而且少見斷頭。它的直徑大約為0.3厘米,保存的總長估計超過50厘米。它的顏色,還顯現著純正的米黃色,具有一定的韌性。”
經檢測,証實這是一碗由小米面和黍米面做成的面條。
王仁湘說:“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分析面條樣品中,還檢測到少量的油脂、類似藜科植物的植硅體以及少量動物的骨頭碎片,應當都是這碗面條的配料,說明這還是一碗葷面。”
王仁湘認為,雖然面條的具體加工工藝還不清楚,但是這個過程中對植物籽實進行脫粒、粉碎、成型、烹調的程序一定都完成了,而且這成品小米面條做得細長均勻。在中國乃至世界食物史上,這應當算是一個重要的創造,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從文獻記述看,面條在東漢稱之為煮餅,魏晉則有湯餅之名,南北朝謂之水引或??,唐宋有冷淘和不托,還有特色面條萱草面。宋代時面食花樣逐漸增多,因為食法的區別,有了一些特別的名稱。《東京夢華錄》提到北宋汴京食肆上的面食館,就有包子、饅頭、肉餅、油餅、胡餅店,分茶店經營生軟羊面、桐皮面、冷淘、棋子面等二三十種。
元代時出現了干儲的挂面。明清出現了抻面和削面。
王仁湘還特別提到了冷面,但此冷面並非我們現在經常吃的朝鮮冷面,確切地說,應該是過水的涼面。冷面見於清代《帝京歲時紀勝》的記述,說夏至當日京師家家都食冷淘面,就是過水面。過水涼面的吃法,早在宋代就很流行。宋代林洪《山家清供》提到“槐葉淘”的涼面,做法本出唐代,杜甫有《槐葉冷淘》詩,詩中道出了涼面的制法,連皇上晚上納涼,也必定叫上一碗冷面來吃。宋代招待大學士,有“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之說,大學士能吃上冷面,也算是一種特別的待遇。
5000年前的烙餅
王仁湘告訴記者,不少考古學証據都說明,餅食在中國史前已經出現多樣化發展趨勢,史前人享受到的美味,比我們想象的豐富得多。他們的盤中餐不僅有面條,還有烙餅、烤餅之類。北方一些地區流行一種現做現賣現吃的小吃,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煎餅果子。
煎餅標准的煎鍋稱為鏊,面平無沿,三條腿。有鏊就有煎餅,由餅鏊的產生可以追溯烙餅的起源。考古在內蒙古准格爾旗的一座西夏時代的窖藏中發現過餅鏊,這件西夏鐵鏊為圓形,鏊面略略鼓起,上刻八出蓮花瓣紋飾,有三條扁足,直徑44厘米、高約20厘米,這是一具實用的鐵餅鏊。
年代最早的餅鏊是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仰韶時期的居民用陶土燒成了標准的餅鏊。1980年和1981年,在河南滎陽點軍台和青台兩處仰韶文化遺址,發掘到一種形狀特殊的陶器,陶色為紅色或灰色,陶土加砂,上為圓形平面,下附三足或四足,底面遺有煙炱。發掘者稱這種器物為“干食器”,以為是“做烙餅用的”,它真的就是陶餅鏊,是仰韶文化居民烙餅的烙鍋。這種餅鏊在這兩處遺址出土較多,說明那裡的居民比較喜愛烙餅。當時烙餅的原料當是小米面。
從考古發現看,中國用鏊的歷史相當悠久,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這也就說明了烙餅的起源,不會晚於距今5000年前,很可能還能上溯得更早,因為陶鏊已是很成熟的烙餅器具。在此之前可能有更簡單的鏊具。西南地區有的少數民族有用石板烙餅的傳統,中原地區最早的餅鏊也許就是用的石板。其實喇家遺址發現的烤爐,就是一架石板鏊,說不定喇家先民也烙過小米煎餅吃呢。
張飛應該吃過標准的餃子
餃子是古代中國人的美食,也是一種文化食品。明代劉若愚的《酌中志》提及,餃子在明宮中稱為“扁食”。說正月初一,“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於內,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據明人張自烈《正字通》說,水餃在唐代有牢丸之名,或又稱為粉角。宋代稱為角子,《東京夢華錄》說汴京市肆有水晶角兒和煎角子。餃子古有牢丸、角子、扁食、水包子、水煮餑餑等名稱,也有稱為餛飩的時候。北齊顏之推有一語說:“今之餛飩,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於是烹飪學界以為餃子起源於南北朝時期,因為這樣的餛飩,其實就是餃子。
明代出現專用的餃子名稱,《萬歷野獲編》提到北京名食有椿樹餃兒,也許是用椿芽做的餡料。清無名氏《調鼎集》中對餃子與餛飩已有了明確的區分。
考古發現的古代餃子的証據,在重慶忠縣的一座三國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一些庖廚俑,有兩件陶塑表現古代廚師正在廚案邊勞作,見到廚案上擺放了食料,有豬羊雞魚,也有一些果蔬等。仔細看去,廚案上還擺著捏好的花邊餃子!這說明在長江三峽地區的三國時期,餃子已成為人們喜愛的美食。這個發現自然就使過去認為餃子起源於南北朝時期的說法失去了意義,而且這是形象標准的偃月形餃子。
在山東滕州薛國古城距今2600年的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在一件隨葬的銅器裡見到一種呈三角形的面食,長5~6厘米,這應當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餃子,只是它的形狀還不算太標准。
王仁湘總結說,在考古發現的大量古代文化遺物中,食物所佔的數量相對要少得多。食物遺存不容易保存下來,也容易被發掘者忽略。同時也受發掘技術與檢測手段和限制,大量的信息沒有採集。其實發掘中可以散見不少歷代的庖廚垃圾。例如舊石器時代庖廚垃圾中的動物碎骨已經石化,研究者在這樣的庖廚垃圾中甚至發現了舊石器居民敲骨吸髓甚至是食人的証據。
沈陽晚報、沈陽網記者 高寒冰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