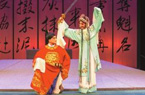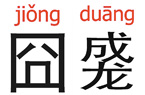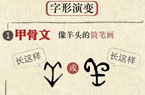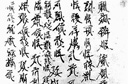近日,洞庭山碧螺春新聞發布會上,一則訊息令人震驚又惋惜:雖然入春以來茶葉產區風調雨順,產量將比去年增加20%,但由於缺乏足夠的採茶工和炒茶師,大量頂級茶葉隻能被留在樹枝上。洞庭山碧螺春茶業協會的統計顯示,目前東、西山共有茶農17458戶,平均年齡超過40歲,其中年輕的本地炒茶工寥寥無幾。青黃不接的手工炒茶絕活面臨困境,茶農們心急如焚:再過20年,誰來炒出頂級碧螺春?
難覓“茶二代”大師
在蘇州東、西山的一萬七千多戶茶農中,有多少年輕人能炒得一手好茶?帶著這個疑問,記者多次前往兩地的茶葉主產區、茶廠集中地區和茶業協會,但調查結果令人遺憾:會炒茶的本地年輕人,有,不多,但基本作為業余愛好﹔能夠水平穩定地獨立炒出幾鍋好茶的年輕人,實難尋覓。西山茶業協會會長周永明說:“東、西山千家萬戶都有茶園,主要是老一輩在炒茶,實在趕不過來了就雇點外地人。小輩們最多隻能幫忙採茶、挑葉。”
32歲的羅雅芬是西山涵頭村人,父母都是茶農,家中有2畝茶園。每到茶葉上市的季節,年過6旬的父母就會進入最忙碌的狀態:患有嚴重腰椎間盤突出的母親要成日採茶、挑葉,而父親在做完一天保安工作后晚上要炒茶直到深夜。羅雅芬告訴記者,自己從小看著父母這樣辛苦,曾想學習炒茶幫他們分擔一些,但最終因為怕燙、力量不夠而放棄了:“殺青時的溫度要高達300攝氏度,並且炒一鍋茶40分鐘裡完全不能停,對女生來說有些吃不消。我隻能選擇其他方式幫他們。”
羅雅芬的經歷在許多本地茶農的孩子身上都發生過,事實上除了炒茶難學外,當地人固有觀念才是阻礙“茶二代”成長的關鍵。“炒茶很辛苦,忙到凌晨4點是常有的事,但普通茶農一年也就賺個五六萬。”羅雅芬對記者說,許多辛苦了一輩子的父母在培養子女的最初就不打算讓他們再“重蹈覆轍”,甚至覺得孩子外出打工比留在家裡炒茶要光榮。“老人們寧願孩子在外地忙得回不了家、讓茶葉爛在樹上,也不願他們再回家做農民。”這樣的觀念如今在東、西山老一輩茶農中依然流行著。
“隻要肯吃苦,哪有年輕人學不會炒茶。關鍵是對於農業的觀念要改變。”生於西山歌月灣的年輕人黃雁萍與羅雅芬的想法不謀而合。
2年前,她毅然把在市區從事金融行業的丈夫帶回西山老家“試驗”:丈夫從未接觸過炒茶,但他體力好、能吃苦、對炒茶又有興趣,他能不能將父親的炒制技藝全部學會?結果讓人欣慰:“最初,他吃了很多苦,手心、手臂、甚至指甲縫中的嫩肉上都被燙出水泡。難得的是他性子慢,願意沉下心來學,兩年下來已經可以獨立炒制。”黃雁萍欣喜地告訴記者,丈夫偶爾甚至能炒出一鍋與老師傅水平相當的茶葉。今年茶葉上市期間,黃雁萍和丈夫依然會在周末回到西山,幫父母採茶、炒茶。
技藝傳承期待扶持
值得關注的是,東、西山能炒得一手好茶的年輕人不多,但願意利用知識特長返回農村、幫父母“突圍”的新生代新型農二代卻越來越多:微信營銷、改良包裝,一批批80后紛紛出手打開了地產農產品現代市場營銷的一扇門。
羅雅芬就是用這個方法在幫助父母。2012年起,她為自己家的茶葉注冊了“今雨”商標,改良了傳統碧螺春茶的包裝,專做高檔茶市場,已經把茶葉賣到了上海、河南、廣東、台灣等地。黃雁萍更是在幾年前就辭去上海一家大公司財務職位,返回家鄉組織周邊的村民一起成立了一家合作社,注冊了品牌商標,線上線下結合,大膽地經營起綠色農業。來自蘇州吳中區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由這批新生代農民主導的網絡營銷方式已佔到東、西山農戶和專業合作社的近1/3。
不過,在農業這根巨大的產業鏈中,脫離了生長這一至關重要的環節是斷然不行的。同老一輩茶農一樣,黃雁萍和羅雅芬這樣的年輕人也意識到了危機。“再過20年父母都老了,炒碧螺春的任務隻能由我們這一輩完成,以我們現在的水平,還能炒出頂級碧螺春嗎?”黃雁萍對記者說,也許未來農民的職業化規范發展、政策扶持等才是吸引進城農民返鄉的關鍵因素。
一家農業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向記者介紹,在法國這樣的農業發達國家,黃雁萍的期待已經部分實現了。雖然法國也面臨年輕人涌向大城市、大農場多由老輩在堅守的相似情況,但那裡農業專業化程度很高,不同領域的農民可以考取專業執業証書上崗、農民到了一定年齡可以退休、年輕人從事傳統農業還享受一些政策優惠等,“因此去大學拿一個農業工程師的學位,再回老家做農場主,其實在法國年輕人中也蠻流行的。”研究人員說,未來茶農的職業化轉型也許是解決碧螺春技藝傳承的較好途徑。 周偉蔚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