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發現”的“南宋西湖全景圖”是清代偽作

“南宋西湖全景圖”(局部)

“南宋西湖全景圖”(局部)

2009年11月14日,羅以民先生在“中美文化對話”論壇上

“南宋西湖全景圖”畫中的紅色洋彩。居民住宅居然緊挨城牆,也不怕殺頭?

杭州西湖宋代蘇堤與今蘇堤的位置圖

“南宋西湖全景圖”斷橋上游人仆役打的清朝高傘,以及橋兩邊的康熙立柱

“南宋西湖全景圖”畫中的大游船是海船,船長而窄,尖底,兩頭高翹
圖文/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羅以民
7月11日,看到《杭州日報》關於陳琿發現美國Freer博物館“南宋西湖全景圖”的長篇報道,十分震驚!
此畫作為界畫(屬工匠類,非藝術),畫工拙劣,通幅皆為偽造的“南宋西湖風景”,其引首和跋尾,也漏洞百出,完全是清代的一幅偽作。這類畫,在清代通常都是為售與富人和洋人而作的。這幅15.81米的偽作,除長度,余與宋《清明上河圖》無可比擬。
現從各方面予以論証。囿於篇幅,所引材料,隻出篇名,不述版本。
1
宋人何以畫出明清西湖?
“南宋西湖全景圖”的開端,畫的是西湖與杭州城的平面圖。僅此,就有4處致命傷:
其一,在杭州城牆靠西湖一側,畫出了清代杭州的城中城、滿城(旗營)的准確位置。
其二,畫出了明代才出現、伸入湖中的“問水亭”。張岱《西湖夢尋》卷四載:涌金“門以左,孫東瀛建問水亭”。孫東瀛,即明代杭州織造、鎮守太監孫隆。而《咸淳臨安志》之《西湖圖》,畫中絕無問水亭。
其三,同為孫隆所造的孫堤,即十錦塘,也出現了,它從清代起,改稱為白堤。
其四,畫中的蘇堤,南岸起點在雷峰塔西數百米,有橋6座,不經過孤山東側,與北岸交接也與今天同。這條蘇堤,為明正德年間楊孟瑛所修(參閱2007年第6期《浙江社會科學》拙文)。而宋蘇堤的南岸起點在淨寺,北接大佛寺(今北山街28號右側是其遺址)。
宋蘇堤的6橋是包括斷橋的,經孤山東側中分西湖﹔而明蘇堤與今蘇堤完全重合,不經孤山,不包括斷橋,北接岳墳東,二八分西湖。兩者南岸的起點相距約900米,北岸終點相距約1800米。
這些明清之景,南宋人何以畫出?
2
畫中蘇堤與宋蘇堤不符
南宋末《夢粱錄》卷十二明確記載,蘇堤是經過孤山抵達北山(即今寶石山)的,共有橋6座:孤山南側4座,孤山北側2座。北側2座分別為涵碧橋(北山第一橋,浙西轉運使陳堯左造,早蘇軾80年)、大佛寺前的孤山橋(又稱保祐橋、斷橋)。“斷橋”是唐朝留下來的(見唐張祜《題杭州孤山寺》),位置應該在今北山街上。涵碧橋和孤山橋,是蘇堤之前連接孤山的唯一通道。宋代還無“白堤”,唐代白居易修的堤在今環城西路至武林門一線,與今白堤無涉。《咸淳臨安志》記載此段“孤山路”至宋末都未更名,不叫堤,更不叫“蘇堤”。
蘇軾造的蘇堤,“八百八十丈”(與章子平書,《蘇軾文集》卷五十五尺牘),宋官尺合今31.6厘米,堤長約2780米,這僅是淨寺至孤山之距離。蘇軾的“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是利用了孤山路的兩座老橋,他實際隻修了4座橋。北山是定指,連偏西一點都不是,稱葛嶺了。
此外,元代杭州人劉一清《錢塘遺事》載:“東坡守杭日筑堤自大佛頭直至淨慈寺前,非為游觀計也。”元代杭州人張雨《貞居先生詩文集》之《孤山記》也說:“山之南蘇堤也!”而今之蘇堤卻在孤山西。
明代皇家的《永樂大典》(殘卷)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更詳盡記載:“當軾開湖時,筑堤其上,自孤山抵北山,夾道植柳,后人思其德,因名曰蘇公堤。其后禁蘇氏學,士大夫多媚時好,郡守呂惠卿奏毀之。乾道中,孝宗命作新堤,自南山淨慈寺前新路口,直抵北山。湖分為二,游人大舟往來,第能循新堤之東崖,而不能至北山。紹興中,始造二高橋,出北山達大佛,而舟行往來始無礙。堤上有亭宇,為游人賞息處。” 該書說此文是從“《杭州府志》引《舊志》”。元代杭州未修志,此“舊志”當推為宋志,惜原書早軼,在殘卷能得此史料,杭人當貴之。由“自孤山抵北山”可知,南宋恢復的蘇堤至明正德前仍經孤山。
因此,“宋蘇堤經孤山”是關鍵。與此不符,可立判為偽作。《咸淳臨安志》在說孤山時,也指出“其西為裡湖”。當時西湖裡、外湖的分界線是蘇堤,分界點在孤山。這是以往的研究都忽視了的。
蘇軾在1090年筑的蘇堤,十年后(1100年)就為政敵呂惠卿奏毀。今天所說的宋蘇堤,是南宋乾道(1168年)后造的。而此間有近70年,西湖上無蘇堤。此間有人繪一幅“無蘇堤”之“西湖圖”,反可能是真品。
今蘇堤全長3300米,肯定不是蘇軾所修。至南宋末年,潛說友修蘇堤全長隻剩下“七百五十八丈”(《咸淳臨安志》),比蘇軾本堤都少了378米,如加上孤山至北山一段,就要少了700米。
所謂的“南宋西湖全景圖”辨別方向稍難,但隻要把它的“蘇堤”6橋,再加上白堤的2橋共有8橋,就不難辨偽了。
3
居然不知宋代西湖有“長橋”
宋代西湖長橋為西湖上第一大橋,長達500米以上,橋上還有三座門。但此畫不僅大圖中沒有長橋,居然連平面圖裡都沒有畫上。萬歷《淨茲寺志》說:
“長橋在寺東一裡,橋頗短。而以‘長’名者,父老相傳舊在白蓮洲(按,今西子賓館內平地,宋代為湖中小洲,趙構曾於此造別墅),橫截湖面水口甚闊,橋分三門,長亙裡許,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旁植桃柳與蘇白兩堤,映帶爭勝。后浸淫填徙,兩涯皆民居矣!”
《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一就記載了李茇“過長橋於竹徑迷路”的事。蘇軾知杭州時的通判楊蟠,就有一首詩《長橋》,說“三島忽相通”,估計指長橋自長橋灣連接了小洲、白蓮洲、中峰(今夕照山,當時在水中),至淨寺。
《西湖游覽志》和《湖山遍覽》也均稱長橋長達“裡許”。宋代還無南山路,人出錢湖門至淨寺,必須從湖面上經長橋。宋楊萬裡“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寫的就是出淨寺大門之所見,閱詩題即知。那時荷花隻有佛家才種,當時滿湖都是葑田,即今茭白田,隻不過古人吃其籽(菰米),今人吃其莖罷了。
宋代西湖的長橋灣還稱“海子口”,“南宋西湖全景圖”的作者如是宋人,怎會對此“壯麗特甚”之橋視而不見呢?
長橋到了明代短了許多,到了清末就沒有了。陳琿說西湖今天與南宋變化不大,此話缺乏起碼的歷史地理知識。南宋時杭州太子灣,方家峪(今海療一帶)皆湖水連天。昭慶寺前(今少年宮廣場)皆水,用許多橋連接陸地。
宋代的石函橋就在今浙江省旅游局大門下,此橋原是寶石山一角海蝕留下的天然岩洞,被“鑿石岡上為行路,下通流水,自然成橋。每視湖水盈縮以為啟閉,舊有閘,其水泄於下湖。今惟橋存,閘廢。”西湖宋代還有上、下湖。此段出自明成化《杭州府志》。
宋代這裡是上、下湖換駁的壩口。林和靖在此處望著孤山的家就寫過詩。西湖為上湖,今保俶路在宋代還是通往下湖的一條河,浙江省政府大院還在下湖的水底。上下湖落差至少3米,康熙時1裡外還能聞飛濺之水聲。
如今此石橋不見了,惟余一“石函路”名,足見宋湖水位高,清代水位降低,才將此石橋廢去。陳橋驛先生早就說過“西湖是個人工湖”,不是歷代浚湖,西湖早就填平了。
南宋初、中期的西湖是在皇城之下,治理遠過北宋,是舉以國之力治湖,水面比今天至少大一半,湖水可直通靈隱,鬆木場,時赤山埠尚可通船,今在山上矣!
4
宋代游人打著清代的高傘?
“南宋西湖全景圖”中,有多處游人仆役打傘,傘柄均高出人一頭,達2米,此高傘為清代康乾時式樣,非宋。傘最初的發明,不是為了遮蔽風雨,而是為了顯示官府威儀,所以又稱傘蓋。要使百姓遠望即知,可肅靜回避,不及者則匍匐道旁,莫可仰視。
宋代用傘更是等級森嚴,《宋史·儀衛志》有祥。民用陽傘在南宋稱涼傘,或青涼傘,傘徑與今草帽同,柄也特短。但律仍禁行人晴天打傘,雖太學生犯事也杖責。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
“鄭昭先為台臣……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為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皂絹為短檐傘,如都下賣冰水擔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邏者猶以為首犯禁條,用繩系持蓋仆,並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責蓋仆。” 雖惹出一場太學風波,擔“傘禁”依然沒有被沖破,連作者葉紹翁也認為不得不“議諸生罪”。此事就發生在杭州。
明成化《杭州府志》也有記載:宋“嘉定中禁士庶不得用青涼傘,多以皂絹為之,特短其檐,止數寸庇日而已,后漸增至尺余者,復嚴行禁約,犯者施行頗峻”。清代則放開傘禁。
該畫者畫出“康乾高傘”,必是康乾之后人作偽。這種長柄大傘傳入日本,至今還在日本使用,中國反而少見了。宋《清明上河圖》畫有傘30余,但均為街頭擺攤的固定傘,路上行人及騎馬官員,有熱得搖扇者,但絕無打傘者。
5
康熙立柱、明清柵欄和大游船
在宋《咸淳臨安志》的“西湖圖”上,斷橋是有亭子的。南宋劉過詩《同許從道游涵碧橋》有“我亭不關鎖”之句,說明斷橋在宋代也是有亭子的。劉過在橋上飲酒達一天,說明這種亭子不小,可供多人聚會宴飲。
但“南宋西湖全景圖”上,斷橋與涵碧橋均無亭子,反在斷橋兩端畫了4根立柱。這4根柱子是拉吊橋起落用的,那是為了迎接康熙、乾隆南巡住孤山行宮加強警衛而設立的。
而南宋皇帝卻未聞在孤山住過一夜。這4根立柱至晚清消失,橋也改為石橋,撤吊橋,設橋門,夜閉。作偽者還看見立柱,當是清中期人。
“南宋西湖全景圖”畫中滿湖柵欄,全是豪強私佔的水面。此情況不可能發生在南宋,試想西湖皇帝常要來游,諸大臣也要游,誰敢私佔。南宋全湖都是放生池,每年四月官府都要率全城百姓來搞放生活動。但明末吏治腐敗,豪強亂佔水面的現象,延續入清。
“南宋西湖全景圖”畫中的“大游船”是海船,船長而窄,尖底,兩頭高翹,這是為抗擊海波巨浪而設計的,吃水深度往往是船高的一半以上,至少2米。西湖水深往往是平均1米左右,旱年則全部干涸。這種船在西湖中不能航行,隻能擱淺。
南宋禁仰視官船,連賈似道在西湖邊的宅子都不許仰視,“否則禍福立見”。在那麼高的游船上俯視官員、甚至俯視皇上后妃,那還了得?
西湖都是平底船。西湖船可以巨大,最大者可達五十丈(宋《東都記勝》),合今150米,相當於護衛艦的長度,但載人也隻有一百余人。為何?因為是平底船。宋代有許多書記載了西湖游船,但絕沒有這種游船。
這種畫法,使我懷疑這個作偽者可能沒有到過杭州,僅是憑看了幾本《武林舊事》依靠資料畫了自己想象中的南宋。
6
偽造的“厲鶚跋”錯漏百出
“南宋西湖全景圖”還偽造了“厲鶚跋”,尤似該畫的“權威鑒定証書”。此“厲鶚跋”洋洋六百言,可謂中國古畫偽跋之最。但卻錯漏百出。
首先,與故宮博物院藏厲鶚真跡比較,就可知這字就不是厲鶚真跡,其內容也不過根據幾本宋代筆記任意編排,但卻能唬住不少附庸風雅,而又沒有真才實學者。
最可笑者,此跋本是為畫主王繩武寫的,但又把本來寫對了的名字錯改為“王承武”。 王繩武確實為雍乾時的揚州商人,但作偽者吃不准,反改錯了。
更可笑的是,造假者居然把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禁傘”的一段意思理解反了。借厲鶚這樣的宋畫鑒定專家之口,說“游人打高傘”反成了鑒定宋畫的鐵証。 厲鶚是《宋詩紀事》和《南宋院畫錄》的作者,當然是“大名頭”。他都懷疑是李嵩所畫,那此畫身價百倍。李嵩何許人?南宋皇家畫院的畫師。但造假者的漢語水平如此低(清代任何一個秀才都不可能犯這樣的錯誤),我真懷疑可能是不熟悉中文的日本人所為。明代日僧雪舟曾在杭州學畫,對杭州非常熱愛,歸國后常對其學生夸我杭州,也畫過不少西湖圖。雪舟愛作長卷,最長者24米,至今存其故鄉博物館。其門前銅像,面向西方,還在望我中國。但雪舟妙品,非此劣畫可比。
在宋代諸多文獻的記載中,“澄水閘”為3橋3閘,可這裡畫錯了,成了獨橋2閘。但最不能容忍的是“厲鶚”居然把“澄水閘”說成是長橋。因為造假者是清代人,沒有看過宋代史料,明明寫著“澄水閘”(泄南山洪水入湖攔泥漿用的,此為官府造),居然也信口胡編。
這個“厲鶚”已經在畫上看見了賈似道的住宅,足見他看此畫到了南宋末。但居然又說:“大石佛院,院之旁曰‘十三間樓’,數之果然”。 這十三間樓本來就是一個傳說,蘇軾離杭后遭到賈易彈劾“以權謀私”而且還“暴孽”,連偌大的蘇堤都毀去,這十三間樓還不毀去,何況這本來就是蘇軾非法的“辦公會所”。此地很快就改成了寺廟“相嚴院”,怎麼會在百年后還“數之果然”呢?
再者,“厲鶚跋”的三方圖章皆偽劣不堪。作偽者完全不知道吾杭厲鶚與丁敬是兒女親家,其能用如此劣貨。丁敬何人?“西泠八家”之首,今“西泠印社”之祖師也,至今多少篆刻兒還不敢望其項背。
7
假“引首”劣墨,洋彩及“和紙”
“南宋西湖全景圖”的“引首”“西湖清趣”4個篆書,是模仿明代大書法家程南雲的,但筆力很弱,臨摹明顯。“翰林侍書”程南雲是皇帝的書法教練和代筆者。他題過大名鼎鼎的《韓熙載夜宴圖》和趙孟頫的《重江疊嶂圖》,可惜這張是假的。
但該“引首”的磁青紙到確實是明代的。其實,這幅字隻要看墨色也可以知道是假的。皇家用墨,黑如漆而亮,此墨淡而稀。普品,程南雲這樣的角色是不會用的。
該畫的顏料紅色妖艷,偏玫紅(美方曾介紹復制品的顏色復制得非常逼真,幾乎毫無二致),乃洋彩,康熙后才舶來中國,與中國傳統的顏料是不一樣的。此畫的紙為“和紙”,帘紋比中國宣紙要細,不但拉力好,而且書畫效果也好,連乾隆也寫詩夸贊。
美國Freer博物館的檔案材料顯示,此畫Formerly attrib. to:Li Song 李嵩 (late 12th–early 13th century),為大收藏家Charles Lang Freer本人捐贈,1911年在中國從陳寬(音)(Provenance:Cheng Kuan, China)手中購得。
但Freer一生並未到過中國,此畫當是別人為其代購,上當就很難免。這個陳寬是否就是造假者並不重要,但此畫的下限可以定到1911年。此畫為標准的日本式現代裝裱,是20世紀該館請日本裱畫師木下與吉裝裱的,卷末還鈐有“木下作品”白文印一方。
該畫上還鈐有“心榖堂珍藏”、“ 心榖□王氏珍玩”兩印,當是偽造的“王繩武”之印。“心榖堂”在中國素無記載,王繩武也不是什麼大藏家。
8
慎莫把“原畫請回杭州”
《疑似南宋西湖全景圖首次在國內亮相》的報道顯然失當,該畫原件一直藏美國Freer博物館,陳琿在最近的鑒定會上,展示的也只是縮小成連環畫大小的數碼照片,何以說是“首次在國內亮相”呢?如果復制品也算亮相,那麼5年前就亮過了。
2009年11月14日,“相約西湖——中美文化對話”論壇在杭州舉行,我作為中方專家發言,對美方提供的一些美國人早期拍攝的杭州老照片作出解讀。
會議期間專門設立展廳,美方將該“南宋西湖全景圖”縮小的復制品(約8米長)展出,並明確說明“斷代為南宋”。午餐,我與Freer博物館書畫檔案部主管戴維·霍格同桌,鄰座是該館長期聘請的中國字畫鑒定專家。
當時我以兩根筷子作比,述說明代白堤、明代蘇堤與宋蘇堤走向的不同。霍格博士聞言大驚,即放下筷子到展廳看畫,良久始歸。我與他們的中國字畫專家談得更多。她返美后立刻給我發來了相關資料,並多次來電交談,囑我發表論文一定要寄給該館。我向其深表敬意。
歸功於這位女專家,霍格次日在浙大會見陳琿,就已將該畫從“南宋”降至明朝了(見有關報道),惹得陳琿還反駁說是宋朝。
打假的文章我5年沒寫,但是今天居然有人要把“原畫請回杭州”,我就不得不寫了。齊白石的畫都賣到了4個多億,那這800年前、又有15.81米長的“航母”(比《清明上河圖》長3倍),沒有5億拿得回來嗎,館藏品恐怕得10億?
可那都是納稅人的血汗,災區的孩子還在危房裡讀書。願君知我。
(來源:羊城晚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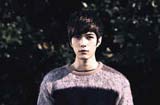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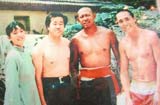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