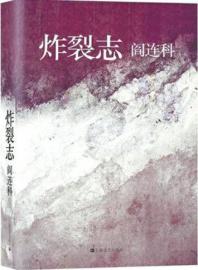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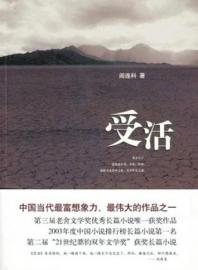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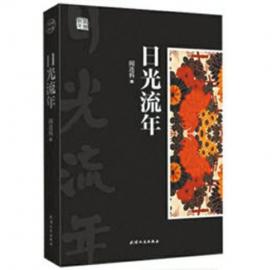

閻連科
5月27日,閻連科獲得第14屆卡夫卡文學獎的消息傳來,引發祝賀聲一片,成為文化圈的關注熱點。卡夫卡文學獎是國際上一個重要的文學獎項。這也是該獎項自2001年設立以來,首次頒發給一位中國作家。他也是繼村上春樹之后第二位獲得該獎的亞洲面孔。
他是誰
閻連科:被國內文學界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的閻連科,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和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應征入伍后從事文學創作,成為專業作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多次獲得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中國文學獎項。代表作品有《日光流年》《受活》《風雅頌》《四書》等,作品被譯成法、英、德、日、韓、西班牙、挪威、丹麥、蒙古等20多種語言。2013年他入列“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
他風格
“神實主義”:由中國著名作家閻連科提出的一種新的文學創作概念,2011年他在《我的現實,我的主義》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這個名詞。即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系,去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神實主義疏遠於通行的現實主義。它與現實的聯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於人的靈魂、精神(現實的精神和事物內部關系與人的聯系)和創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的特殊臆思。
“我完全不知事情是怎麼發生”
新華社5月28日專電河南籍著名作家閻連科獲得2014年度弗蘭茨·卡夫卡獎。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得此獎項,也是繼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之后,亞洲第二位作家獲此殊榮。消息傳來,面對紛至沓來的恭喜和祝賀,閻連科28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完全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對該獎的推薦、評選一無所知。”
他表示,將於10月底前往捷克布拉格接受此獎項以及1萬美元的獎金。“獲獎只是三天五天的事情,過去就過去了,不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和寫作。”
對閻連科作品頗有研究的著名學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梁鴻說,“閻連科用富於想象力的文學手法,描述著中國生活的復雜性、荒誕性。”閻連科的獲獎在中國文學界引起較大反響。有學者認為,近年來,莫言、余華、閻連科的文學作品相繼在國際上獲獎,反映了國際文學界對漢語寫作和中國作家的重視,有利於中國文學在世界領域的傳播。對此,閻連科認為,不是一兩個作家在國際上獲獎,中國文學就“走出去”了。中國文學能不能真正走出去,要看這些作品能不能影響到國外的讀者、能不能影響到不同語種人們的寫作。閻連科說,“擴大中國文學的影響力,還需要更多的作家認真低下頭來寫出自己的作品,其他的不要考慮太多。”
多點了解
卡夫卡文學獎諾獎風向標?
卡夫卡文學獎,是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獎之一。捷克政府為紀念出生於布拉格的西方現代文學宗師、德語小說家弗蘭茨·卡夫卡,於2001年設立。每年評選一次。主要頒給那些作品具人文主義關懷的作家,獎金1萬美元,同時授予卡夫卡雕像,獲獎者不存在國界限制。
歷屆獲獎者均為世界級“大牌”作家,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200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耶利內克和哈羅德·品特,都曾在獲卡夫卡獎后獲得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因此該文學獎又被業內稱為“諾獎風向標”。
閻連科則因其“荒誕現實”色彩的寫作,被普遍認為是,繼莫言之后最有希望獲諾獎的中國作家之一,不過,多次入圍國際文學獎的閻連科昨日在回答華西都市報記者採訪時態度淡然:“簡簡單單吧。無論獲什麼獎,該干啥還是干啥,該寫作還是寫作。”閻連科昨日也向華西都市報記者確認,他將在10月26日前往捷克布拉格接受此獎項以及1萬美元的獎金。
【報喜】
閻連科一無所知
“無論什麼獎,該干啥還是干啥”
昨日上午,華西都市報記者多次撥打閻連科電話均無人接聽,后來他主動給記者發來短信解釋說,“這會兒家裡人多,不方便接電話。”對於獲獎的感受,他回應說:“實在無話可說,簡簡單單吧。”面對其他媒體記者的提問,閻連科的回應也同樣簡單:“無論獲什麼獎,該干啥還是干啥,該寫作還是寫作。”
在幾個月前,華西都市報記者曾面對面採訪到前來成都舉行讀者見面會的閻連科,其中專門談到對獲文學獎的看法,他說,“我認為,一個作家對待文學獎項的最好態度,應該是順其自然,把它當成是‘天上掉餡餅’性質的事情,真被餡餅砸到頭上,那就接下來。如果沒有被砸到,那千萬不要跨越一步伸手去接,寧肯它變成一堆垃圾。”
另據記者了解到,閻連科其實對自己入圍卡夫卡獎和最終獲獎整個過程,一無所知,“直到前幾天,我收到卡夫卡獎評委會的一個郵件,信中問我,如果獲獎了今年10月份是否有空去布拉格領獎。我當然很高興地答應了,但我想估計他們給每個入圍作家都發了這樣的郵件。”也是直到那個時候,閻連科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進入了卡夫卡獎評選中。
【道喜】
麥家、蔣方舟很興奮
“他得這個獎,實至名歸”
中國作家首次獲得如此重要的國際文學大獎,很多讀者都表示振奮,不少作家同行也紛紛表示祝賀,蔣方舟在微博上說:“祝賀閻連科老師獲得卡夫卡獎!去年得獎者是阿摩司·奧茲,村上春樹、菲利普·羅斯、耶利內克也都是該獎的得主。太開心啦!”昨日華西都市報記者也聯系到蔣方舟,談及她對閻連科作品的認知,這位80后作家表示,“我跟閻老師太熟了,讓我來談閻老師的作品,估計會顯得不那麼客觀。我就純粹表達一下,為他高興吧!”
除了從蔣方舟這樣的新生代作家同行獲得知音,閻連科的作品在他的同輩作家同行中,也獲得足夠的理解和尊重。湖北省作協主席、著名作家方方認為,“閻連科近年寫了不少反映變形社會、怪誕人生的作品,與卡夫卡氣質很相近。”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麥家昨日也對華西都市報記者說,“得獎是好事。現在不是在鼓勵作家走出去嘛,得國際上的文學獎,不但‘走出去’了,而且還‘走進去’了。而且,我覺得閻連科得卡夫卡文學獎,是非常貼切的。我是閻連科的同行和朋友,同時也是他的讀者。他的作品,我基本都認真讀過。在我看來,閻連科最近5年的寫作,對現實進行極度的夸張和變形,這跟卡夫卡文學世界的荒誕和變形,精神和氣質是吻合的。他得這個獎,實至名歸。”
【討喜?】
出版人駁斥“經營說”
“這個獎公信力很強”
99讀書人的資深文學編輯、英國老牌文學雜志書《格蘭塔》中文版主編、英語文學譯者彭倫,對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國外出版的情況很熟悉。28日,他向華西都市報記者介紹,卡夫卡文學獎,是一項獎勵對象真正跨越國界的國際性文學大獎,“很多外國的文學獎項,多是限制為獎勵本國或本語種的作家。目前在世界文壇,國際性的文學獎並不多,像諾獎、卡夫卡文學獎,這些是國際性質的文學獎,在獎勵作家時,不分作家的國籍。而且,這個獎不是獎勵作家哪一部作品,而是獎勵作家,有一種終身認可的意味。所以顯得很可貴。”
就在閻連科獲得卡夫卡獎的消息傳出后,有網友提出質疑:這會不會是“經營”出來的?對此,彭倫在網上直接給予反駁,“這種獎是經營不來的。”在與華西都市報記者探討這個問題時,彭倫說,“卡夫卡文學獎這種文學獎,公信力是沒有問題的,他的評委很多,閻連科不太可能都認識捷克的評委們吧。”華西都市報記者張杰
“我希望在我最好的寫作時期裡,能讓我如魯班那樣最后創造、設計出木牛流馬圖紙來,讓我找到那全新、完美的我,並且,還要像諸葛亮那樣制作、創造出一個、一架文學的木牛流馬來……”——閻連科某次公開演說
獨家對話
閻連科:寫作擔心兩件事
處處表揚,無聲無息
華西都市報:在你看來,文學作品最可貴的品質是什麼?你的作品具備這些品質嗎?
閻連科:最可貴的品質就是絕對的個性化,用自己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目前我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以后的寫作還要進一步努力。
華西都市報:對於同年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你看得多嗎?你判斷作品好壞的標准是什麼?
閻連科:看了不少,但不會那麼及時去看,一般都是喧鬧之后找來看。我判斷小說的標准非常狹隘,非常不可取。關於一部小說的優劣,對我來說,是你小說中有哪些部分和文學元素,是我無法取代的,是我經過努力也無法完成的。就是說,我喜歡看那些我的寫作無法表現和無法達到的作品。我認為,我無法完成的作品,對我來說,都是好作品。莫言、余華、王安憶、賈平凹、韓少功等,他們在藝術上都有不可取代的地方。莫言的《酒國》,裡面紅燒小孩當然是虛幻的想象,但他這種充滿了奇特歡樂景象的想象,我做不到﹔看《長恨歌》,字裡行間那種簡潔、准確和適宜,以及扑面而來的詩意,我是做不到的﹔《許三觀賣血記》那種悲痛下面的溫暖我也做不到……這些作家你就得尊敬他。因為在他的作品裡有你無法完成的元素。我判斷作品好壞隻有這一個標准,就是他能做到,我不能做到。
華西都市報:你現在閱讀情況如何?能不能談談你的讀書經驗?
閻連科:我有充分的條件和時間來讀書和欣賞各樣的小說,各樣的書籍,可惜已經沒有了少年時生吞活剝與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讀書變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讀書在許多時候,會成為一種負擔。讀書似乎就是為了寫作,每讀一頁,都期望從中抓撈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沒有,就覺得是一次沒有意義的閱讀旅行。還有,總是試圖要把閱讀變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運中的經歷,可結果,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再有,如今書是越讀越少,閱讀人的靈魂,卻反而越來越多﹔對閱讀變得苛刻挑剔,而對人際世事,也愈發地苛刻和挑剔。總而言之,我現在的讀書經驗不可取,太功利了。
華西都市報:你平時寫作,是整體框架構思好才動筆,還是一邊寫一邊想?
閻連科:無論長篇、中篇、短篇,對我來說最初就是一個念頭,仿佛星星之火,漫長的構思就是燎原的過程,沒有什麼規矩可言,一般也沒有寫作提綱,但是會有一個大概的方向和路線圖,在腦子裡的呈現,這個路線圖更多的時候是故事和人物。
華西都市報:每一部新作問世后,你最擔心的是什麼?
閻連科:對我來說最擔心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處處充滿著表揚之聲,一種是無聲無息。
華西都市報特約記者吳懷堯
析
【為什麼是閻連科?】
“他是受關注被爭議,不是因爭議才被關注”
在不少讀者的印象中,閻連科的作品在國外文學評論界,較為顯眼。他的文學作品曾先后入圍法國費米娜獎、亞洲布克獎、塞萬提斯獎等國際文學獎。雖然最后未能獲獎,閻連科還曾為此自嘲自己是“陪跑”角色。但是,能連續受到如此多的文學獎項關注,已經是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
為什麼閻連科的作品能易於受到國際上各種文學獎的青睞?對此,英語文學譯者彭倫對華西都市報記者分析說,這裡面有多種因素,“比如,閻連科的作品,一向有很好的國外出版基礎。國外很多出版社都很喜歡閻連科,引進、翻譯、出版他的作品比較多。這就是一個優勢。比如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很多都是捷克人,而閻連科的作品就有捷克語版本。他的作品受到這個獎項評委的關注,也是自然的。”
對於閻連科的作品,復旦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陳思和曾經評論說,“閻連科天生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又是當代中國最具探索勇氣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從不重復自己的寫作經驗,每一部都具有小說形式的探索性,開掘著新的令人喜悅的思想深度。他是備受關注而被爭議,不是因為備受爭議才被關注。”
資深出版人陳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閻連科的作品在法國出版后,無論是書評、媒體採訪還是與讀者見面,大家最關注的還是文學本身、文本本身,“所有評論文章的都是強調文學上的創新。如果以為一個中國作家可以完全憑借非文學因素,躋身世界文壇,這是低估了策劃人和出版人的文學鑒賞力和對文本判斷力,低估了西方媒體和讀者的文學眼光。”
閻連科也曾經回答該問題時說,“肯定有人會說,我能得獎可能跟爭議性有關,但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就像我的一些書在國外出版的時候,讀者問的還是,小說為什麼要這樣寫,他們關心的真的還是創作、藝術本身。”
華西都市報記者張杰
讀
【怎樣理解閻連科?】
“用虛構和神話的手法寫實”
2013年末,閻連科來到成都為其最新長篇小說《炸裂志》做宣傳,詳細闡述了自己創作《炸裂志》的構思、心得和理念。
閻連科以神實主義的寫作手法,荒誕、夸張地呈現了一個百人鄉村走向超級大都市的變遷,將經濟發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兩性博弈,家族的仇恨,歷經滄桑依舊溫暖的無功利的堅持,融合在了一起。有評價說,“這是一部鄉村志,也是一部精神史和心靈史。”有評論家說,“他被現實的瘋狂性和內心的憤怒壓倒了,沒有力量去推開。”“心狠手辣的寫作太多了。”但也有評論者說,“閻連科如果沒有憤怒,還是閻連科嗎?他劍鋒偏,但也可一劍封喉。”
張杰
大獎留名
2001年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
2002年捷克小說家伊凡·克利瑪
2003年匈牙利小說家彼得·納達斯
2004年奧地利小說家、劇作家耶利內克(當年獲諾獎)
2005年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當年獲諾獎)
2006年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
2007年法國詩人伊夫·博納富瓦
2008年捷克小說家阿諾什特·盧斯蒂格
2009年奧地利先鋒劇作家彼得·漢德克
2010年劇作家、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韋爾
2011年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
2012年捷克女作家和文學理論家達妮埃拉·霍德羅娃
2013年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
2014年中國作家閻連科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