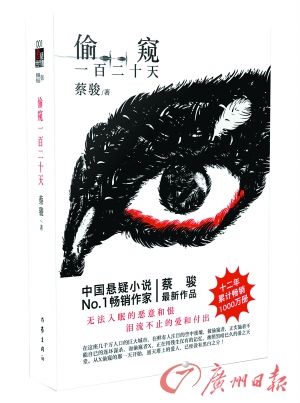
《偷窺一百二十天》

蔡駿
網絡作家十年
2000年3月,蔡駿模仿王小波風格在榕樹下網站貼出他人生中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天寶大球場的陷落》。不曾想,僅10年時間,蔡駿從浩瀚的網絡寫手中脫穎而出:連續10年保持中國懸疑小說最高暢銷紀錄。其系列小說銷量早已突破1000萬冊,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懸疑小說“教父”。
蔡駿的成名不過十余年,卻佔據著中國懸疑界絕大部分的市場。成名以來,每部貼上蔡駿標簽的作品都能夠成為當年的暢銷書,系列作品的品牌效應已經顯現。
蔡駿:男,1976年生於上海,中國最受歡迎的懸疑小說家。作品總銷量突破1000萬冊,並連續10年保持中國懸疑小說最高暢銷紀錄。
自述簡歷:我沒有讀過正規的大學。19歲在上海郵政上班,那是在1997年。2005年,我忽然發現通過寫作,已足夠可以養活自己了:一年寫小說掙來的版稅,已經超過了單位發給我工資的幾十倍。但上班已成為了一種習慣。我小學時的夢想是當一名考古學家,中學時想當畫家,還痴心妄想地考過美院,最后才誤打誤撞地成為一個作家——至今我仍對“作家”兩個字感到汗顏。
“懸疑教父”如此煉成
蔡駿小說以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嚴密緊湊的邏輯思維見長,在歷史與現實、愛情與驚悚、懸念與推理之間展開故事,探尋深邃命題。
他出道靠的是獲得了“貝塔斯曼”文學新人獎,而后長篇小說《病毒》的橫空出世才真正打響了懸疑小說的招牌。蔡駿說,“因為離不開母語的土壤,於是固執地認定漢語是地球上最美的語言,並誓言以漢語寫出世界上最好的小說。”
梳理其創作成長之路:從2001年第一個長篇《病毒》開始,到《幽靈客棧》止,這一段時期他的作品注重恐怖氛圍的刻畫描寫,情節上比較傳統,更偏重於氛圍的營造和人物宿命論,而對情節的科學性做了比較淡化的處理,這段時期的代表作品為《貓眼》和《詛咒》。
第二個階段,可以說是由中篇小說《荒村》為發端,進而延伸出來的一整個“荒村系列”作品,其中包括后期創作的《旋轉門》、《蝴蝶公墓》以及《瑪格麗特的秘密》。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蔡駿創作的黃金時期,這也使得蔡駿憑借“荒村系列”大紅大紫,奠定了“中國懸疑第一人”的稱謂。
第三階段則是以《天機》為標志,及往后的《人間》、《謀殺似水年華》、《沉默獸》到《地獄變》漸漸趨於成熟,蔡駿不再單純地注重恐怖元素的運用,而是走上了偵破懸疑的路線,更加著力於人性的挖掘和探索,此中翹楚是《天機》和《謀殺似水年華》。
第四階段,2013年出版《生死河》曾獲得本報主辦的“中國圖書勢力榜年度好書”等各種大獎,蔡駿開始華麗轉身,悄然向嚴肅文學靠近。今年8月作家出版社重磅推出《偷窺一百二十天》,奠定其為“中國懸疑小說教父”地位。
蔡氏小說席卷銀幕
評論認為,蔡駿小說特點非常明晰,比如他多部作品的主人公叫“葉蕭”。
天下霸唱和南派三叔都是屬於“盜墓派”懸疑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受環境的局限還是比較大。而蔡駿的筆風靈秀生動,花樣多變,近至浙江、上海,遠到英、法,上到幾千年前的良渚文明,下至當前社會生活,幾乎都有所涉獵。 蔡駿的小說的特點,是別人想模仿都模仿不來的。
蔡駿不僅小說暢銷,而且他的小說被改成影視劇之后也取得了不錯的票房和收視率。2004年,《詛咒》被拍攝為電視連續劇《魂斷樓蘭》﹔2007年8月,由《地獄的第十九層》改編的電影《第19層空間》上映﹔2008年8月,由《荒村》改編的電影《荒村客棧》上映。這些影視劇在市場上均有相當的號召力。可以說,蔡駿開辟了中國現代懸疑小說的先河,又是現代懸疑小說集大成者。
打造中國懸疑文庫
第一品牌
在採訪蔡駿時,記者獲悉,蔡駿聯手作家出版社將陸續推出的“懸疑世界文庫”,旨在打造中國第一類型小說文庫。
蔡駿在聊到策劃“懸疑世界文庫”初衷時說,現在市面上已有的一些懸疑小說文庫,要麼完全是舶來品,與中國社會現實毫無關系﹔要麼水准良莠不齊,讓讀者誤以為懸疑小說就是恐怖低俗。他策劃文庫的目的就是要讓讀者讀到真正的懸疑精品。
好的懸疑小說不應該隻有推理和設計,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贖》打動讀者的是最后的救贖和解放,東野圭吾的《白夜行》讓人動容的是凶殺后悲慟的守望。這些深入人心的作品都體現了命運的懸疑性,正可謂“懸疑無界,故事無常”。這也是“懸疑世界文庫”所體現的“命運有無限種可能”。
社會懸疑小說門檻太高?
目前,中國懸疑小說跟歐美甚至日本對比來說,隻有蔡駿一枝獨秀。那麼懸疑小說在中國文壇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有多少作家在創作懸疑小說?具有社會派懸疑風格的作家,創作現狀如何?
蔡駿就此表示,“我可以算是在中國最早有意識地創作社會派懸疑小說,我不知道之前是否有其他作家這樣嘗試過,至少我是第一個明確提出這個觀念的。但是,社會派懸疑小說的創作門檻相當高,必須要求創作者首先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這在中國已經是少數了,尤其是在類型小說領域。”
“其次是創作者要對生活有深入的洞察力,能夠把握社會問題的本質,這一點不是初出茅廬的新人可以做到的﹔最后就是懸疑小說本身就很難寫,要把一個故事寫得很圓滿和精致,又要表達出作者的世界觀和信仰、態度,三者相加就是難上加難了。所以,現在我能見到的成功的社會派懸疑風格的作家還非常少。但是,我希望通過我的寫作,能夠產生大量的讀者基礎,讓更多的人願意來嘗試這種寫作,未來在中國也一定會涌現出更多優秀的社會派懸疑的作家與作品。當年,日本也是從無到有走過來的,從第一部的《點與線》開始,而恰巧當時的日本社會與今天的中國社會高度相似,我們正處於一個社會問題的題材寶庫之上,這是一個大時代,是中國作家的幸運。”
幕后推手:
神秘“23”女網友
蔡駿用十年時間寫作,作品銷售過千萬,已經顛覆了傳統作家寫作的概念。在其身后,推動其創作、銷售的推手不乏沈浩波、黎波、黃雋青等出色的民營書商和伯樂。但蔡駿認為,真正推動他創作的幕后推手是一個神秘的女網友。
蔡駿說,“2000年12月下旬,我與一位榕樹下的女網友‘23’在IRC(當時一種網絡聊天工具)上聊天。她建議我寫一些可讀性更強的作品。我想起了鈴木光司的《午夜凶鈴》系列小說,我跟她打賭說自己也會寫好這類小說,至於賭注是什麼早已忘了。為了與‘23’的賭約,我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病毒》。那年榕樹下,我寫的都是富有想象力的純文學作品,獲得過‘貝塔斯曼·人民文學新人獎’。而‘23’的人氣幾乎與我不相上下,而今回想恍然如夢。幾天后,2000年12月24日平安夜,上海美琪大戲院,第二屆榕樹下網絡文學大獎賽頒獎典禮上,我見到了‘23’,我們在路上聊了一會兒,才知道她還在讀大學。平安夜的傍晚,十幾個人在南京路上談天說地。當我們要去唱歌時,‘23’翩然告辭。這是我見到她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第二年,《病毒》在網絡上發表。而蔡駿不再上網聊天,“23”也不再上網發表作品。蔡駿依然在寫他的懸疑小說,第二年《病毒》出版。而促使《病毒》誕生的“23”,卻仿佛中了病毒,就此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他說,“2012年9月,在中國的一個正午,在美國的一個午夜,我找到了她——她與我相距十二年的時間,相差1.2萬公裡的空間,如果,命運的旋轉是以十二年計算的話,我相信這是造物主的安排。”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