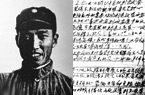◎張慧瑜
電影是一門成全年輕人的藝術,與年齡和閱歷沒有特別直接的關系,有的導演拍了一輩子電影,可能處女作就是其最高成就了,因為電影創作除了需要個人才情,也深受時代影響,陳凱歌就是這樣一位導演。《黃土地》(1984年)至今是一部在藝術和社會意義上兼具開創性的作品,它的產生得益於上世紀80年代的文藝氛圍。上世紀90年代,陳凱歌借助香港投資拍攝《霸王別姬》(1993年),摘得戛納金棕櫚獎。新世紀,為了回應WTO的挑戰,中國電影進入產業化時期,陳凱歌經歷了《無極》(2005年)的慘敗后又嘗試拍攝《梅蘭芳》(2008年)、《趙氏孤兒》(2010年)等。可以說,面對不同的電影環境,陳凱歌努力做出調整,拍出與時代相契合的作品,但他的情懷和糾結又使其趕不上時代步伐。
啟蒙與無法啟蒙的故事
1984年陳凱歌執導、張藝謀攝影完成的《黃土地》,被視為第五代登上歷史舞台的代表作。那時,他們是剛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年輕人,作為“文革”后的首批大學生而受到制片廠和文化界的期待。他們用嶄新的電影語言回應了時代的文化命題,最初也是為了命名第五代才使用了代際導演的說法,之前的四代導演都是參照第五代追溯出來的。這種導演中心論與其說來自於法國新浪潮的作者電影,不如說得益於模仿蘇聯建立的大制片廠制度(與好萊塢制片人中心的制度不同)。
《黃土地》講述了外來搜集民歌的八路軍無力拯救愚昧、落后的黃土高原村民的故事。相比八路軍顧青帶來的婚姻自由、斗地主、分田地等革命理念,大全景中黃土地和天空對人形成了強烈的擠壓,這種巋然不動的、壓抑性的黃土地在上世紀80年代的語境中是幾千年封建專制的象征,是靠天吃飯的庄稼人宿命。與《白毛女》中喜兒從“舊社會把人逼成鬼”到“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解放之路不同,《黃土地》中渴望擺脫包辦婚姻的翠巧沒有等來公家人,即便唱著“鐮刀、斧頭、老?頭,砍開大路工農走”的新民歌也沒能渡過黃河。這是一個無法啟蒙又召喚新啟蒙的故事,就像結尾處逆人流而上的男孩憨憨預示著一種新的希望。這種對空間造型的運用、對戲劇化的排斥等視覺化處理被認為是回歸電影本體的體現。
1986年陳凱歌、張藝謀聯袂制作的第二部電影《大閱兵》也延續了這些風格。影片講述了年輕士兵克服各自的困難參加國慶閱兵的故事,用近景鏡頭中被分割的身體來表現不同的個性,用全景中整齊劃一的步伐和軍姿來呈現集體主義的儀式感。這部並不太經常被談起的電影顯示了第五代的空間美學轉化為國家認同的潛質,這種閱兵般的宏大場面在第五代后來執導的古裝武俠大片和國家慶典(如2008年奧運會)中經常使用。
1987年陳凱歌改編阿城的小說完成了《孩子王》,講述知青老杆去做鄉村教師,卻對這種啟蒙者的角色充滿懷疑,並對傳授新知的教室空間進行了批判,正如老杆教給學生唱的歌:“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裡有個老和尚在給小和尚講故事,講的什麼呢?從前有座山……”代表著一種歷史的循環往復。老杆在黑板上寫下一個誰也不認識的天書般的漢字以及學生王福對字典的盲目抄寫的行為,都說明知識、文字不再是文明的象征,而是另一種蒙昧無知。這不再是文明啟蒙愚昧的故事,而是對以文字為代表的現代文明(漢文化)的反思。最終老杆被趕出學校,來到一處仿佛能夠聽到遠古回聲的神秘之地。
如果說《孩子王》借邊緣、異域的空間講述了一個反啟蒙的故事,那麼1991年完成的《邊走邊唱》也是一部反啟蒙寓言。電影中一位被村民稱為神神的盲人琴師不僅無法拯救自己的徒弟,反而最終發現彈斷千根弦后找到的藥方不過是一張白紙。《邊走邊唱》又回到了《黃土地》式的命題:歷史是循環的、無法改變的。這些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歷史文化反思運動有內在的呼應關系。
歷史的人質與人性邏輯
上世紀90年代,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電影生產陷入困境,獲得國際電影節的認可成為吸引海外電影投資的重要方式。
與第五代拍攝老中國或專制中國的故事不同(如《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挂》等),1993年,陳凱歌改編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小說,制作完成了講述現當代中國歷史的電影《霸王別姬》,借京劇演員段小樓和程蝶衣的人生際遇呈現從北洋軍閥到“文革”結束的歷史。從程蝶衣被妓女母親送到戲班學戲到譽滿京城,他的人生像被歷史綁架的人質一樣,隻能被動地接受一次次歷史的強暴,直到“文革”中被徒弟、師兄出賣。
相比上世紀80年代的啟蒙主題和寓言式書寫,《霸王別姬》更像個人與歷史的悲喜劇。這種個人作為歷史人質的表述來自於用人性來批評大歷史的暴力,個人不再是歷史的參與者,也不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個人只是歷史的受害者、親歷者和旁觀者,就像解放前段小樓、程蝶衣和老太監站在北京街頭木然地看著解放軍入城一樣。這不僅吻合於一種用個人、個人主義來敘述歷史的模式(如1987年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執導的《末代皇帝》),也吻合於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終結后關於中國作為封建帝國和專制國家的想象。這種個體陷入歷史紛爭的故事在《風月》(1996年)中也有體現,幽暗的家族隱秘、封建大家族的回歸、個人無法把握的命運,這些都成為老上海懷舊和風韻猶存的民國故事的經典橋段。
1998年,陳凱歌執導了中國與日本、法國聯合制作的史詩大片《荊軻刺秦王》。秦始皇的故事是世紀之交中國電影的熱門題材,1996年第五代導演周曉文拍了《秦頌》,2002年張藝謀拍了《英雄》。相比歷史上秦王被書寫為慘無人道的君王,第五代電影開始為秦始皇“翻案”。他們作為“文革”中長大的一代,經歷了造反、弒父和 “撥亂反正”、文化反思之后,對權力(歷史)的態度是曖昧的,這也體現在《荊軻刺秦王》中,陳凱歌用秦王嬴政和刺客荊軻來代表兩種主體位置。嬴政雖然是一國之君,但也是歷史的人質,這不僅指他小時候在趙國做人質,后來在繼父呂不韋的擺布下成為秦王,更重要的是嬴政秉持列祖列宗“平定六國,一統天下”的祖訓處死呂不韋,也就是說,秦王要放棄個人的所愛、所恨,通過弒父來變成歷史遺囑的執行人。相比秦王無休止的殺戮,荊軻則代表人性的力量。電影一開始冷血殺手荊軻就放下屠刀,誓不殺人,甚至為拯救孩子的性命而願受胯下之辱,最終荊軻同意刺秦也不是為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壯舉,而是為了心愛的女人趙姬。這種歷史不可違背的宿命和人性的邏輯使得這部電影在敘事上充滿裂隙。
歷史的和解與個人成功
新世紀伊始,以張藝謀《英雄》的商業成功為標識,中國電影進入產業化時期,電影生產和放映實現市場化,電影人的渴望由對國際電影節的藝術加冕轉向獲取國產高票房。《英雄》的意義不只是創造國產古裝武俠大片的商業類型,而且回應了《荊軻刺秦王》留下的歷史悖論。在《英雄》中,荊軻式的刺客不必再糾結於殺人還是不殺,秦王也不必陷入個體與強暴者的焦慮,刺客主動放棄了刺殺以自我閹割的方式規勸秦王早日統一天下,隻有這樣才能使天下太平、百姓免予涂炭。這種對權力的自我臣服對於陳凱歌來說並不容易化解。
2005年,陳凱歌花巨資制作了一部魔幻古裝武俠大片《無極》,這部據說改編自莎士比亞《麥克白》的電影講述了個人與宿命的故事。不管是大將軍光明、奴隸昆侖,還是北公爵無歡、王妃傾城都是被命運捉弄的人,他們之間的愛情建立在一系列誤認和欺騙之上。電影的票房失敗與其說是這些哲理化的理念與商業片的邏輯無法融合,不如說是導演給每個角色都設定了可以被寬容的理由,沒有絕對的善惡,從而無法產生真正的戲劇沖突。
經歷了《無極》的市場教訓后,2008年,陳凱歌拍攝了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傳記片《梅蘭芳》,講述了舊時戲子成長為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藝術家的故事。從年輕時的大膽創新成為京劇名角,到20年代末登上美國劇院獲得滿堂彩,再到抗戰時期保住民族氣節,這些都體現了梅蘭芳始終不忘大伯關於紙枷鎖以及爺爺臨終前提升伶人地位的告誡。相比《霸王別姬》中程蝶衣以藝術的名義為日本人唱戲,梅蘭芳則擁有了獨立品格和藝術自信,成為拒絕為日本人演出的愛國藝術家。由此可見,這種上世紀80年代以來個人對歷史的控訴轉化為一種個人成功的美國夢故事,這也許是這部影片叫好又叫座的原因所在。
與《梅蘭芳》相似,2010年陳凱歌拍攝的歷史片《趙氏孤兒》也是把個人放置在歷史的風暴眼中。這部電影被清晰地區隔為兩部分,前半部分講述程嬰遭遇“宮廷政變”而被迫卷入歷史漩渦的故事,后半部分則是“化仇恨為愛”的故事。程嬰成了趙孤(子)與屠岸賈(父)之外的角色,既在歷史之內,又放逐在父子秩序之外。相比荊軻(反抗者)與秦王(權力者)之間的對抗,程嬰既不認同權力的位置,也不認同於刺客的位置,程嬰試圖實現權力者與反抗者之間的和解。面對巨大的歷史暴力,不管是梅蘭芳,還是程嬰都不是“挺身抗暴”或“殺身成仁”的英雄,但他們也並非歷史的受害者和犧牲者,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主動面對歷史的困境,這代表著一種新的個人與歷史的主體狀態。
從影30載,陳凱歌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探索片、上世紀90年代的國際電影節電影以及新世紀以來的商業大片等不同的電影制度。相比很多導演主動適應新的電影環境,陳凱歌有自己的歷史糾結和文化困境,這使他的電影很難順滑地實現轉換,這也是其電影的文化價值。面對過於商業化的電影環境,對於陳凱歌來說,如何實現從一名電影作者(藝術家)變成與產業、市場相契合的電影制作人依然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文/張慧瑜(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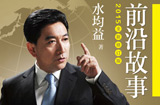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