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在北平的漢學家與中國學者的合影,自左而右依次為:方志浵、傅吾康(Wolfgang Franke)、Woelters、法國出版商Vetch、Hope-Johnston、楊宗翰、Franois Cleaves、艾鍔風(Gustav Ecke,手中抱著他家佣人的孩子)、艾鍔風家中的佣人、衛德明(Hellmut Wilhelm)。此照片由傅吾康的女兒傅復生(Renata Franke)女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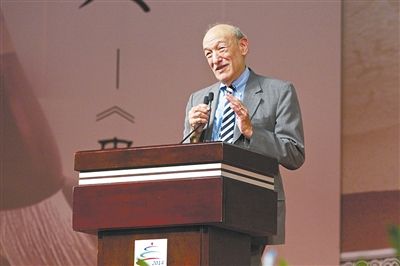
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做開幕致辭。中國人民大學供圖
9月6日,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舉行,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義、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校長巴泰雷米·若貝爾等來自38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專家學者出席大會。
世界漢學大會由孔子學院總部和中國人民大學共同舉辦,本屆大會主題聚焦“東學-西學400年”,各國學者就東西文化展開交流,回顧了漢學的開端、流變。而在“青年漢學博士生論壇”中,我們也在青年漢學學者的研究中看到了漢學的新意思。讓我們跟隨漢學家們的視角,一起回顧世界漢學的一段往事,一起感受漢學發展的新主題。
馬禮遜、比丘林
傳教士漢學的先驅者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亞斯尼科夫教授描述了兩位傳教士在1816年的一次會面:當年,英國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團訪北京時,馬禮遜是隨團的中文秘書兼譯員,途中,與一群騎馬的歐洲人相遇,彼此用法語進行了交流,這群人是俄國東正教的傳教團,他們的首領就是比丘林。
其中的這位隨團譯員馬禮遜就是第一個將《聖經》譯成漢語的英國漢學奠基人,而被認為漢學史上“珠穆朗瑪峰”的比丘林是俄羅斯中國學和東方學的創始人,被米亞斯尼科夫認為是“第一個全面研究漢學、將俄羅斯人文研究與西歐漢學傳統成功結合”的學者。
米亞斯尼科夫將兩人進行了很多對比,“比如他們同一年——1807年到達中國,兩人都是傳教士,中文都不錯,而且他們都開發了中國語言的語法書:中英或者中俄的辭典。再比如兩人回國后的不同命運:1924年,馬禮遜回到英國,受到了國王的接見,在倫敦的精英圈極受歡迎,並在當時激起英國人對中國的興趣。而比丘林1822年回到了聖彼得堡,在當年9月4日被關押於瓦拉姆修道院,在那裡呆到1826年的11月份。同年,馬禮遜回到中國,這一年比丘林邀友人普希金一起到中國,可是被普希金拒絕了。”
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巧合。比丘林寫了一本書叫《北京描述》,馬禮遜則寫了一本描述廣東港的書等等。
米亞斯尼科夫介紹,比丘林最主要的一本書是晚年寫就的《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這部關於中亞各民族歷史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融會比丘林對中國的國民狀況、民風民俗的觀察,比丘林關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和一些結論后來也成為了俄羅斯研究中國人民族志心理學的科學基礎。“正是由於他採取了這種全面的研究方法,20世紀漢學就已經分為歷史、哲學、語音學、藝術和其他學科。”
德國“流亡漢學”
推動現代學科在中國大學的建立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頒布臭名昭著的《重建公務員隊伍法》,把種族歧視法律化和國家化,大批重要漢學家因自己或配偶是猶太人被當局開除出大學或驅逐出境,或是不願與納粹合作而流亡到其他國家,直接造成了德國漢學史上缺失的一代。其中包括著名的漢學家子西蒙、科恩、白樂日、哈隆、申得樂、衛德明和埃伯哈德等人,離戰火最遠的美國是首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誕生地的北平也成了漢學家的重要選擇。這批漢學家在歷經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后,先后離開中國。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李雪濤看來,這是美國二戰后漢學研究崛起的重要因素。
“從德國的角度來講,這些漢學家移民中國(此后大部分去了美國)后來被學界視作是人才的流失,但同時也推動了國際漢學以及中國自身學術的建設和發展。”在李雪濤看來,這是一種學術能量的守恆。德國漢學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異常頻繁,這也得益於當時中國學術界精英的支持,這些學術界精英大都是既有國學根基又受到過系統西方教育的學者。
當時在中國居住的德國漢學家與中國學者之間的互動,已經不僅限於共同翻譯中國典籍,這些交往還包括三十年代成立的北平“中德學會”。福華德、傅吾康、霍福民和謝禮士這些漢學家,都曾在中德學會度過對自己漢學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年月。而中德協會中方的董事有:丁文江、袁同禮、胡適、傅斯年、賀麟等著名學者。
李雪濤認為,來自歐洲的漢學家們對中國的重要影響並不僅僅在漢學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學科,這些漢學家在本國都受到過不同學科系統的專業訓練。以聖言會的神父鮑潤生為例,他從1933年起在北平輔仁大學所擔任的是社會學系主任以及歷史學教授。受過嚴格德國學術訓練的鮑潤生,秉承了萊比錫學派的學術傳統,將系統的社會學的知識講授給了輔仁的學生。“在用西方的學術理路將傳統中國學術納入近現代的西方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方面,西方漢學家們的著作實際上是第一步的嘗試。正是仰仗這批德國漢學家的努力,使得很多學科很早地就在中國的大學中建立起來了。”
轉型之路
漢學如何從“古代”走向現代
二戰前,同在中國的漢學家還有美國人費正清。正是在這位與很多中國學者有著深厚友誼的美國漢學家手中,漢學在美國完成了從歐洲傳統漢學到中國學的范式轉型。
“二戰后費正清對漢學有一個夢——不僅僅是他,還有美國幾個大學的代表,他們站在一個社會科學委員會組織的角度,提出了一個新想法:漢學應該進入美國大學的主流。”在開幕致辭上,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說,“這裡的很多中國學者應該算是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特別是1977年高考的受益者,二戰以后美國開放了一些政策,我認為我也是一個受益者。”
傅高義說,二戰以前,漢學家們在美國、在歐洲研究中國古代的事情,但是費正清那一代的學者認為,我們應該了解世界,他們的夢是美國大學主流的歷史系、政治系、經濟系、法學院、社會學系與人文學系都有人專門研究中國。“那個時候他們沒有人通過社會學研究過中國,當時我很年輕,費正清先生培養我,做一個社會學系的中國學者。”
但真正跟中國交流要到1964年之后。“基辛格來到北京以后,我們美國人慢慢可以跟中國有交流的。所以,我們1971年以前沒有辦法向中國學習,但是1971年以后我們有這麼個機會。”傅高義第一次來到中國是1973年,跟隨一個自然科學代表團來訪中國。“我們外國漢學家基本的工作、基本的責任是讓外國人能夠了解中國,我認為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努力,跟很多的學者一起向中國學習。”傅高義說他也有一個漢學夢,這個夢就是“讓中國學者發揮自己的作用,和外國學者交流。讓我們看到盡可能多的材料,與中國學者交換看法,提高對中國的理解。”
B06-B07版撰文/新京報特約記者 李昶偉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