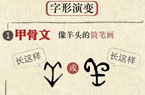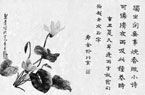甘陳聯軍滅郅支
呼韓邪單於求做漢家女婿
甘、陳率領的多國部隊,兵分六路,先后到達了康居的東部邊境,在距離郅支城三裡的地方駐扎下來。隻見城上立有五彩旗幟,數百精壯甲士在登城守備,還有幾百名騎兵在城牆下往來奔跑,幾百名步兵在城門兩邊布下像魚鱗一樣的陣勢,另有一百多名騎兵奔沖向甘陳聯軍的駐地。甘、陳二人不為所懼,有條不紊地指揮弓箭手張滿弓面向敵人,這些騎兵見漢軍訓練有素,十分懼怕,便不戰而退了。隨后,甘、陳二人帶領軍隊包圍郅支城,箭雨從漢軍的隊列射向城牆上的人。雖然土城牆外邊還有一層木城牆,兵士從木城牆中向外射箭造成了部分漢軍傷亡,不過漢軍很快點燃了木城牆,迫使木城牆內的敵人退入土城牆內求援。
此時,登城迎戰的郅支單於被射中了鼻頭,身邊的夫人們也傷亡慘重。郅支單於不得不跑下城牆,且戰且退,最后退到了自己的內室。最后,郅支單於受傷而死,被軍丞假侯杜勛斬下了首級,漢軍順利攻破了郅支城。
此后,北匈奴的力量被嚴重削弱,再也不能對漢朝構成威脅,南匈奴呼韓邪單於見狀,又喜又懼,上書請求入朝覲見,並表示願做漢家的女婿。於是才有了我們熟悉的“昭君出塞”故事。
在這場戰役中,步兵在城下演習的魚鱗陣法和土城牆外增設一層木城牆的筑城方法,在此前關於中原和匈奴的記載中均未見,相當奇特。西方漢學家德效騫(Homer H· Dubs)教授以為,這裡的“魚鱗陣”就是羅馬軍團善用的一種陣法——龜甲陣,即士兵用緊密相接的盾牌在軍陣的上方和四周形成堅固的盾牆以使軍陣刀劍不入,彼時在郅支城下演習的步兵,當為羅馬士兵﹔而在土城牆外增設的木城牆,也類似於羅馬士兵以尖木樁御敵的軍事防御方法,有可能郅支城在修建之時就有羅馬士兵參與其中。若誠如此說,這場戰役就是兩千多年前西漢與羅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軍事交鋒,這兩個當時世界上最強的大國,遠比后世想象的更早就有了交集。
“羅馬軍團”的來龍去脈
不遠萬裡而來的“志願軍” 或許只是雇佣兵
﹝2﹞影片中羅馬的統治者為克拉蘇,其子享有繼承權,為典型帝國形態。然當時羅馬實際處於共和國時期,影片中兩位王子之父克拉蘇與龐培、凱撒合作,組成政治聯盟,選舉兩位執政官主導政治,不存在世襲享有唯一帝位的統治者。
﹝3﹞影片中此時羅馬與安息的聯姻與結盟在真實歷史中並不存在。
看到這裡,也許您就會奇怪了:羅馬和漢朝相隔近半個地球,在交通條件落后的兩千年前,怎麼會有羅馬士兵不遠萬裡來到匈奴,幫助郅支保家衛國?這批“志願軍”為什麼要跨越千山萬水進行這場“國際援助”?
要解答這個問題,需要將視野拉大,看看此時在地球的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實際上,在甘、陳聯軍出發前不久,遠在千裡之外的羅馬共和國﹝2﹞也進行了一場遠征。公元前53年,羅馬共和國敘利亞行省總督克拉蘇在未經元老院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入侵安息帝國﹝3﹞(Parthian Empire,或譯作“帕提亞帝國”,位置大約相當於今伊朗),遭到慘敗,克拉蘇本人被殺害,羅馬軍隊中的大部分士兵也都在戰爭中陣亡或被俘。德效騫教授認為,克拉蘇軍隊中的部分羅馬士兵可能突破了安息騎兵的重圍,為求生存,他們充當當時西域各個國家的雇佣兵,最后來到郅支城中,教郅支單於的手下筑城術與兵法,並在隨后甘、陳二人突襲郅支的戰役中與漢朝軍隊相遇。
郅支城之戰,漢軍大勝,據史書記載,這場戰役共俘虜一千余人。這些幫助匈奴對抗漢軍的羅馬士兵,幸存的想必也在這一千余人之內。那麼這批人如何安置呢?德效騫教授又大膽假設:西漢張掖郡有驪靬縣,據《后漢書·西域傳》,大秦(羅馬古稱)又名犁鞬,二者同音,故“驪靬”乃羅馬之義,驪靬縣就是郅支麾下羅馬士兵降漢后的居留地。經過數千年的時間,他們的后代已逐漸漢化,在生活方式上與周圍人無異,但他們仍保留有高鼻深目的歐洲人外貌特征,象征著自己羅馬人后裔的身份。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