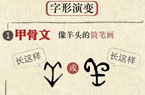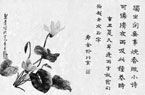人藝版 《萬尼亞舅舅》劇照。
【編者按】今年是契訶夫誕辰155周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以一出《萬尼亞舅舅》作為開年大戲。該劇日前在北京上演,無論是演員表演,還是舞美設計,都被導演打上了實驗性質的烙印,也因此在業界和觀眾中引發巨大爭議。支持者認為該劇展現了對白的獨白性,而這正是契訶夫作品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特點﹔反對者則質疑該劇對形式的追求大過了內容。
本版今日刊發李建鳴的文章,雖然談的是《三姐妹》,但對於圍繞《萬尼亞舅舅》而起的爭議,卻能提供新的啟發。
還記得二十年前,有一位現在已經是著名導演的女士曾問過我以下問題:“既然斯坦尼曾把《三姐妹》排得那麼成功,后人照他排就是了,為什麼還要重排?”從她的目光來看,非常真誠,所以絕非兒戲之言。我多少有點措手不及,隻能講了一些有關導演戲劇和二度創作的話,供她參考。今天,這個問題似乎已經不是問題,導演必須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釋來演繹古典名著和新作品,成為大家的共識。究其原因,首先是思想開放,此外,國外經典舞台作品的引進,也起到了直觀啟發的作用。以契訶夫的作品為例,近年來,國內導演對他的關注越來越多,搬上舞台的實驗也似乎不斷,國外引進的版本也時而可見。這一現象引起了不少劇評人的關注,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依我所見,盡管俄羅斯文化對國人,特別是歲數大一點的人來說,並不陌生,但是和莎士比亞或易卜生的作品相比,契訶夫的戲劇作品對中國人來說,應該是難以駕馭的。因為他的戲劇人物是俄羅斯某個歷史階段的一種特定類型:慵懶、消極、愛做白日夢,多少有點自私。但又帶有生活在那裡的人的一些永恆的特征:愛激動,愛討論,愛失望。這些人物的生存環境也很糟糕:農奴制度的土崩瓦解,工業革命的姍姍來遲,都給他們個人生活帶來危機感。在這樣的情況下,空談和抱怨就成了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這樣的人物對世俗感很強的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所以在舞台上看到他們,也很難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再加上有些導演似懂非懂的處理,使契訶夫的戲劇作品成為乏味的代名詞。
我想,在對契訶夫的作品進行二度創作中,經常會看到以下二種偏差。一個是把喜劇演變成悲劇,另一個是把契訶夫同托爾斯泰混淆。先來說說前者吧。契訶夫生前對當年莫斯科劇院對《三姐妹》的處理十分不滿,他反復強調這部作品的喜劇性。那應該如何理解他的這一觀點呢?首先,當然要理解喜劇的含義是什麼?這些年國人習慣把喜劇同小品聯系在一起,引人發笑就成為了喜劇的唯一特征。我的理解是契訶夫之所以把《三姐妹》理解為喜劇,是因為這些人物無休止的抱怨和等待(喃喃自語)已經變成他們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用現在的話來說,都是些強迫症的特點,但這些人物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嘮叨中度日的習慣,而正是這點賦予這些人物特有的喜劇性。喜劇性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自我呈現和自我意識之間極大的反差,光從呈現的語言來看,自然會得出悲悲戚戚的結論。但如果著力表現他們對脫離現實的渾然不覺,才會使舞台產生喜劇的效果。我相信,對契訶夫來說,這些他熟悉的人物不會讓他感到痛苦,而隻會讓他感到好笑,因為這些人永遠跳不出自己的陰影,只是在自己的陰影下跳舞,不言而喻,這一定會產生一種哭笑不得的喜劇效果。
去年,我看到的美國集市運動劇院來華演出的《三姐妹》,久久讓我無法平靜,因為他們對《三姐妹》的理解和表現太到位了。在他們的演出中,人物身上的那種庸俗性確實會引人發笑,伊蓮娜“去莫斯科”的喊叫聲成為演出中的一種節奏,而不是內心痛苦的叫喚。即使在結尾,當悲劇發生,軍官們離去,哥哥的破產,所有這些情節也都是順理成章的出現,成為習以為常的事件,因而也就不會產生傷感。編導在最后用三姐妹對未來的更好的展望,使這部作品徹底失去了悲劇性。
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我所見到的契訶夫的絕大部分演出都會給我一種錯覺,那就是舞台上的人物更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女性:高貴、漂亮,充滿神秘感。我很早以前在德國看的《三姐妹》就是典型的這樣一次演出。三姐妹穿著華麗、風度翩翩、輕盈的台步,舉手投足都流露出貴族氣息。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導演的錯覺,導演並沒有真正了解那些生活在俄羅斯外省人的真實環境:多半都沒有自來水,道路泥濘,幾乎沒有什麼消遣,生活也相當拮據,正是種種不切實際的願望和當下生活的尷尬之間的強烈反差形成了一種喜劇性。當然導演對托爾斯泰筆下女性的鐘愛,也是導致他們進入誤區的原因。還有一種可能性是他們要把契訶夫有些乏味的劇本在舞台上搞得有聲有色。通過對契訶夫舞台作品所做的簡單分析得出的結論就是:導演在進行二度創作時,對原作的精華一定要有到位的認識,尤其是國外的名著,否則的話就會讓觀眾看了一場似乎熱鬧和精彩的戲,但過后會不知所雲。我在北京曾經看過名聲赫然的《建筑大師》,演員的表演可謂精彩,舞美也令人刮目相看,只是對劇本的理解使我頗有微詞,因為劇組把易卜生試圖描寫“大師與上帝的對話”,變成了“凡人與凡人”的對話。這原本是表現人的信仰的作品,現在卻變得模糊和不確了。
導演當然有權在二度創作中表現自己的意圖,傳遞自己的聲音,只是這種意圖和聲音一定要清晰,正是這一點,對導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要了解原作品的背景和劇作家的意圖外,還要找到與現實的聯系。另外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導演必須了解人的心理,所以也必須具備現代心理學方面的知識。這對導演古典名作尤為重要,例如執導莎士比亞的作品。隻有對人的心理和人與人的關系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幫助演員去完成這個角色。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導演的世界觀尤為重要,因為除了懂舞台所必需的技術外,導演必須有對自己和對世界清醒的認識,隻有這樣,才能把握古典,並在古典和現實之間找到一條呈現劇作的藝術道路。
(作者 李健鳴 系翻譯家、劇評家)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