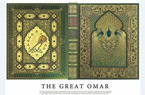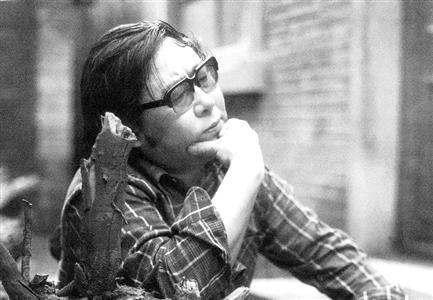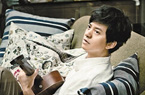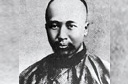酈國義(文藝評論家、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成功的啟示 自覺的機制
我想起《平凡的世界》小說出版的過程,和今天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拍攝過程中的遭遇有些類似。路遙認為,不同的讀者閱讀的感受層面是不一樣的,不同的讀者需要各種不同的創作方法,隻有深刻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才能被廣大的不同層面的讀者所接受。
電視劇可能比小說創作更不容易。一部文學作品是作家一個人的創作,但是電視劇創作,面臨著市場的競爭,面臨著讀者審美感受的不同需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堅持不但需要像單蘭萍、主創隊伍的志同道合,營造良好的創作環境,背后還需要資金的支持。
單蘭萍九年前貸款買小說《平凡的世界》的電視劇改編權,按照創作過程來說,這是在題材的選擇階段,單蘭萍有她的眼光,有她的情懷,有她的魄力。
第二階段是改編創制攝制的生產過程。在今天的制作圈有這麼一句話,有了好本子,錢就蜂擁而至。這是一個誤區,在這個階段,資本的投入是以逐利為根本目的的,所以錢未必能夠保証文化導向。它可以是一個文化產品或者文化商品,但是它不能保証理念的成功,不能保証主流價值的成功。在這個階段,上海市委宣傳部給予了投入,這是為了保証他的文化價值。
第三個階段是播出階段,播放平台抱著什麼樣的理念、什麼樣的價值觀,在什麼時段什麼頻道播出,是很有講究的。
第四個階段就是我們的評論和傳播,需要精心組織評論。
怎麼把這四個階段我們所做的東西變成自覺的機制?我希望從事文藝創作組織引導服務工作的同志,能夠從路遙《平凡的世界》的寫作和電視劇的制作過程中得到一些啟示。
尹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昨天的現實主義
30年前的小說改編后,為什麼能夠在兩家衛視的平台上播出,而且在互聯網上有近20億的點擊量?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我們重拍20世紀80年代的經典作品,可能因為這部劇成為一個趨勢。這個趨勢意味著什麼?我有兩點想法。
第一點,昨天的現實主義變成今天的理想主義。路遙過於傳統的現實主義寫法,在當時受到了一些批評,但是今天恰恰是這種現實主義,顯示了它跨越時間的一種生命力。這個生命力不僅來自於故事所講述的那個年代,20世紀70到80年代的青年人非常敏感自尊,這樣的一群人物不僅是一代青年人的寫照,也是中國人的一代青春記憶。為什麼今天還重拍?我特別佩服支持者、創作者和投資者的眼光,這種眼光不僅是一種人文擔當,它有一種驚人氣質是一脈相承的——人活著得有點精氣神。少安少平兄弟為解除困難而奮斗,活的有困難有價值。一開始,大家都覺得這部劇是老人家對於過去時代的回憶,后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觀看這部劇,在互聯網上追這部劇,它不僅僅是對一代人的青春的回憶,而且是對我們稀缺的某種東西的補償。
第二點,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講,青年人不缺正能量,而缺喚醒這種正能量的可能,隻要我們有機會是可以喚醒這種正能量的。我們從這個作品中看到,真正能夠觸動他們靈魂的東西在哪裡。這個東西非常值得研究,特別感謝創作團隊對原著的尊重,帶給了它稀缺性,無論有多少爭議,從這點上來講都值得我們欣慰。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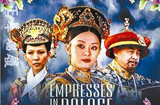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