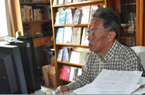□曾立平
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創意旅游紀念品“朕知道了”膠帶風靡一時,這幾個字是復制於康熙回復給大臣的密折中的真跡。你知道嗎,在該院收藏的那些清代密折中,就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發自南京的親筆,是直接遞到皇帝手裡的,內容也大多與南京息息相關。
給康熙的密折是專奏專聞,即時批復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有一個《知道了:硃批奏折展》。“知道了”是皇帝批閱大臣奏折的常用語,“硃批奏折”是經皇帝親自用硃砂批閱的奏折原件。
據曾昭英文章介紹,從康熙開始,清朝就建立了“密折”制度。這是隻供皇帝一人專看的,比作為國家機密的軍機處檔案更為機密。正常折子交給通政司審閱后再呈交,特別長的,還會由大臣寫“貼黃”,即附黃紙,概括要點。而康熙的“密折”則是專奏專聞,不經過通政司,直接遞到皇帝手裡。折面上不寫奏者姓名,隻寫“南書房謹封”字樣。康熙即時批復,他一度右手有病,強用左手批復,毫不耽誤,一則防泄密,二則可以深入了解真相。
1924年溥儀出宮后,人們發現一個小木箱,內藏一批康熙朝的密折,主要是包括曹寅在內的三個江南織造上的奏折。這三人都是宮廷內務府旗人,全部親筆繕寫密折,短小精密,匯報內容由民情世風到雨水收成,不一而足。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展出的硃批奏折時,筆者意外發現了幾份大約300年前由“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謹奏恭請聖安”的奏折,細看內容,也都是與南京這個昔日明都息息相關的。
詳報“明孝陵西北角塌陷”事件,以防“謠言流播”
在一份“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寫於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708年7月12日)的“謹奏恭請聖安”的奏折中,他向康熙報告了兩件事,其中一件是關於明孝陵的:
“江寧洪武陵塚上西北角梧桐樹下,陷塌一窟口,面有伍尺余寸、深約貳丈余,下視如井。臣念洪武陵有御賜碑額,太監看守。因民間訛言塚已塌下,臣隨往勘驗,離地宮尚遠拾伍丈余,毫不相關。原系當先培填之土不堅,日久,值雨沖塌,水流寶城之外。當有地方該管官員,即命陵戶挑土填平。恐謠言流播,訛傳失實,有廑宸衷,合先奏聞。”
稱洪武陵而不稱明孝陵,是避諱“明”字。“民間訛言塚已塌下”事關重大,因此時離南明永歷帝1661年被吳三桂絞殺才47年,“反清復明”的暗流仍在民間涌動。離1681年剿滅吳三桂也才27年,人心是否安定也未可知。為此,康熙還曾專程謁洪武陵,立“治隆唐宋”碑,以籠絡人心。
更為嚴重的是,那一兩年江南地面不平靜,康熙在曹寅奏折上的硃批,也擔心“又聞盜案甚多”。曹寅在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1707年10月15日)的一份奏折中向康熙解釋說:“盜案原系浙江舊案,鼠竊狗偷之輩。當時匿家光福山中,轉攀拿獲,自知不免大戮,恐該衙門動刑痛苦,遂妄為大言,使問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時之累。緣巡撫遠出蘇城,又無老成之官,一時城柵過於嚴防,以致百姓驚慌。其實不過尋常盜案,並無連海結伙不軌之事。后恭聞皇上聖諭,責地方以不加查察盜案,凡臣民無不歡忭,以為天鑒如臨,明洞萬裡。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理合一並具摺奏聞,伏乞聖鑒。”
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708年3月22日)奏折中又解釋說:“臣聞得四明山通福建,歷來盜賊之巢穴,此輩皆在別省行劫,歸藏山中,形跡幽秘,其來已久。以前未嘗不犯,問官隻問眼前現在之案,不株連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為百姓有買米下海之謠,又巡撫中軍分兵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紛擾,故問官詳據口供。令蒙皇上差各大臣嚴審,將來自可窮絕根窩,永無夜警。至於奸僧一念委給付之事,即如晌馬賊歃血拜盟一類,皆由於地方官員柔弱懶惰,誠如聖諭‘不勤不慎’所致。當此天下富強之時,大臣靜妥任事,小吏勤慎奉公,何務不辦。瑣細小事,動輒上聞,或借此掩飾,見其勤勞。或借此密奏,見其親近,亦未可定。安能逃皇上洞徹萬裡之明,終於自誤而已。所有百姓情形委細,未免字逾常格,臣謹具列奏聞。”
曹寅認為這件事本不大,只是鼠竊狗偷之輩,恐衙門動刑痛苦,妄為大言,使問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時之累。而地方官員辦事不力、虛張聲勢,造成百姓驚慌。而且他認為,瑣細小事,動輒上聞,或借此掩飾,見其勤勞﹔或借此密奏,見其親近。
盡管如此,有些客觀現實是回避不了的。這從曹寅附在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十二日(1708年5月2日)開?折內的“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折”可見端倪。此案涉及的“朱三太子”,民間傳說是崇禎的三兒子,是“反清復明”的一面頗具號召力的旗幟。其實,早在南明弘光小朝廷就鬧過“太子”案,但那個“太子”不管真假,已經被降臣送給清軍,沒想到又冒出個“朱三太子”來。好在康熙已得到消息,他硃批道:“山東地方將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勢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不久,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708年6月4日)奏折中也奏報了“朱三太子”在魯獲解的消息。
由於以上這些種種不安定因素,故而曹寅聽到“洪武陵塚上陷塌一窟口”的消息后,不敢怠慢,立即“隨往勘驗”,並“恐謠言流播,訛傳失實,”使皇帝內心焦急,就將勘驗情況和處理結果及時向皇帝報告。康熙在奏折上硃批:“知道了,此事奏聞的是。爾再打聽,還有什麼閑話,寫折來奏。”
康熙的硃批肯定了曹寅的報告,並且要他繼續打聽,隨時上報,可見康熙對這件事也是相當重視的。至於“陵塚上西北角梧桐樹下,陷塌一窟口”是否“當先培填之土不堅”?還是另有“暗道機關”?這就要文物專家去考証了。
四個“萬囑”,體現多疑康熙對曹寅也有一片真心
由康熙與曹寅之間的密折可以看出,曹寅這個江寧織造還要執行一些直接來自康熙的特殊旨令。
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709年10月1日),曹寅密折報熊賜履病故,康熙批:“知道了,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若何?爾還送些禮去才是。”曹寅復奏:“遺本系病中自作。聞其遺言,命墓江寧淳化鎮之地,不回湖廣。”康熙硃批:“聞得他家甚貧,是真否?”曹寅回奏:“湖廣原籍有住房一所,田不足百畝。江寧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畝。江、楚兩地房屋約值七八千兩。”康熙又批:“熊賜履遺本系改過的,他真稿可曾有無?打聽得實再奏。”
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是康熙朝一代重臣,理學家,時人常稱他“清廉剛介”。此前康熙和曹寅之間密折中就曾多次提到他。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708年3月22日),曹寅在奏折中向康熙報告:“臣來時蒙聖諭令臣存問原大學士臣熊賜履,已於二月二十日往湖廣拜掃,俟其來時傳旨。”當年四月初一日(5月20日)的奏折中又說:“任大學士臣熊賜履,於本月初一日回江寧,即至臣處,跪請聖安。臣將前存問之旨宣訖,熊賜履望闕叩頭謝恩雲:‘臣惟有全家頂戴感激天恩。臣自湖廣來,一路太平無事。’隨即回家。”由此可見生前,康熙對熊賜履是禮敬有加的,誰知其身后康熙還有那麼多問號在等著他。
由此想到另一件值得一記的事。康熙五十一年七月(1712年8月),曹寅染上瘧疾,他讓李煦密折上奏,向康熙討藥。當時治瘧疾最好的藥是西洋進口的金雞納霜(奎寧),但即便以曹寅之富有,也難以搞到。
康熙立即批復:“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瀉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納霜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除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
四個“萬囑”,從北京到揚州,康熙派快馬趕去,也算一片真心,雖然最終曹寅還是不治而亡,但這也算是一段佳話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