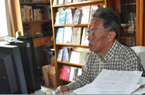■劉林源執著研究,希望得到專家的回復。
一首《木蘭詩》,千古傳誦,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家喻戶曉。河北元氏農民劉林源發現,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這篇課文中用的是“願馳明駝千裡足”,而后則成了“願馳千裡足”,且課文解釋避開駱駝之說,將“千裡足”說成了千裡馬。“明駝”跑哪兒去了?二十年來,他查詢資料,深入鑽研,持續向有關部門反映此事,卻很少引起關注。
講述
教女兒讀課文時 發現“明駝”跑了
劉林源,1956年生,河北省元氏縣北褚鄉西褚村農民。自幼喜歡讀書,父母不識字,家裡連一冊連環畫都沒有,他經常逃學一整天,到供銷社廢品站守著,偷人家收上來的舊書。1956年人教版的幾冊初高中《文學》課本,就是他那時擁有的。劉林源小小年紀,從中感受到了《木蘭詩》(亦名《木蘭辭》)的魅力。
劉林源一直讀到1973年底高中畢業,那時課本上沒有《木蘭詩》。所幸高中歷史老師古文基礎深厚,經常在課堂上背誦一些古文。劉林源正是從老師聲情並茂的朗誦中,深切感受了“願馳明駝千裡足”的語言韻致,異族風情。
迫於生活壓力,劉林源有20年沒怎麼看書。1994年,上小學五六年級的女兒借閱別人的中學語文課本,劉林源在一旁指導教她朗誦,突然發現這一問題,課文中的“願馳明駝千裡足,送兒還故鄉”,成了“願馳千裡足,送兒還故鄉”。“明駝”怎麼沒有了?
劉林源開始給教材出版社、媒體寫信反映,希望有人關注此事。那時郵費便宜,挂號信才兩毛錢,一年下來也不過十塊八塊。他連續不斷地反映,可是沒人回信,沒人理他,令他漸漸陷入苦悶,一耗就是十年。郵費也越來越貴,妻子開始抱怨。“我作為一個農民,雖然研究詩詞不耽誤農活,總歸是不務正業。我不敢與老婆生氣,怕村裡人笑話,更不敢拿小賣部公用電話去說這事。”昨日劉林源告訴記者,直到2000年后,家裡裝了座機,經過電話反映后,才引起電視台的關注,但沒幾天又陷入沉寂。他也陷入深深的苦悶。
打工之余 查閱資料深入研究
劉林源有四個孩子,為了養家糊口,農閑時他到各地建筑工地打工。有一段時間,隻要沒事了,他就逛報攤書店,買不起,就到處翻看,查找有關信息。經常整晚失眠,思索誰能給他解釋,從哪兒找人家的郵編電話。“后來,我終於找到人教社語文編寫室的電話,打通之后,對方對我的諸多提問,就一句話‘我們有古本依據’。”劉林源說,人教社《語文》新課本注明該文選自《樂府詩集》,1956年老課本注明的也是選自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他們沒提到明駝,就解釋為千裡馬。而老課本解釋“明駝”,就具體引証了《酉陽雜俎》之說。“我一個農民,上哪兒去考証啥古籍版本呢?我就一部七十年代購買的《辭海》。”劉林源說,“在我看來,明駝代表鮮卑的民族風情,地域特征。”
劉林源仍不放棄,為了給相關部門反映,他騎車幾十裡上縣城打印店,花14塊錢打印論文,再一一寄過去。“有人回話說,看不懂你想要說什麼。然后就再不接我的電話了。有的人讓我找古籍研究單位。”劉林源說,有時在省會轉了幾家單位后,才發現兜裡的錢,隻夠買長途車票了。他隻得步行趕往長途汽車站,到了縣城,再連夜走回家。
雖飽受挫折,但劉林源仍堅持研究,搜集資料,改寫論文,翻看在鄉下能找到的所有書籍。“我又給《文學評論》編輯部打電話,正好是王保生老師接的。他聽不太懂我鄉音很濃的口語,明白我是個農民后,他說話慢下來,一種我從未感受過的和藹、關切之情,充滿他的話語。他覺得我的研究有道理,還給我寫了親筆信,寄贈了他們出的刊物,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劉林源說,后來他又向《文藝報》、《咬文嚼字》等報刊雜志投稿,編輯老師都給予肯定,但劉林源的文章不符合報刊發表的體例……
“幾年下來,這些研究論文經了很多編輯之手,一直發表不了。我一個鄉巴佬在痛苦中掙扎,很多老師不嫌棄我之淺陋,寄來研究資料,給我很多鼓勵。”劉林源說,“不敢說越挫越強,我這人就是有點?。我相信,沉默的証據總在事實這一邊。否則,我不可能從一個本來對此一無所知的鄉下人,僅憑推想,就能一路尋到‘明駝’這個原點性問題上。”
今年天津《散文》雜志第四期,刊發了劉林源以筆名漢梓撰寫的文章《明駝 故鄉 女兒情》。那時,他正在建筑隊裡給村民蓋房子,搬磚、和泥。
觀點
明駝是鮮卑族風情物語
劉林源認為,《木蘭詩》乃北魏時鮮卑民歌,廣為流傳。最后,由北宋郭茂倩收入《樂府詩集》。上世紀五十年代,葉聖陶等人曾校訂幾冊《文學》,作為中學語文課本。人教版1956年初中《文學》第四冊,就收編有《木蘭詩》。該詩第五段的末兩句為“願馳明駝千裡足,送兒還故鄉。”課文下有注:“明駝,就是駱駝。據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說,明駝是能行千裡的駱駝。”但是,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至今,我們的《語文》課本,卻堅拒“明駝”於千裡之外,將此二句作“願馳千裡足,送兒還故鄉。”甚至,將千裡足解釋為千裡馬。
其實,不僅五十多年前的《文學》課本裡有“明駝”。還可在朱東潤所編《歷代文學作品選》之《木蘭詩》中欣賞到“明駝”。葉文玲《洛陽詩韻》所引《木蘭詩》句也有“明駝”。而金庸1965年所著《俠客行》,更以“明駝”為一種意象,命名了一些武功招式,如“明駝駿足”等。那麼,何以這些文學大家都信賞“明駝”,而如今的《語文》課本卻堅決抵制呢?
鮮卑民族東漢時壯大,佔據蒙古草原、甘肅等廣大地區。而這一地區,正是亞洲雙峰駝的產地。在鮮卑文化中,“明駝”當是早有的一種風情物語。而漢人耕戰,向以牛馬為驅。兩相比較,“明駝”是該詩的民族特征與地域風情的真實存照。《辭海》1979年版,明駝:“善走的駱駝……屈足漏明,則行千裡。”
劉林源認為,有此“明駝”,才能是送兒還故鄉,才能是鮮卑兒女的故鄉情懷,才塑造出千古絕倫超然永世的藝術形象。試想木蘭回鄉之路,沙丘碧草,藍天白雲,山川遼闊,金曦流溢,壯士英姿,明駝神駿,別一番氣度雍容,別一番異族風情,豈秦漢文人之千裡馬所能構此佳境!一首《木蘭詩》,一段女兒情。生死歸望,鮮卑故鄉。舍此明駝,何復可當!
就此,記者聯系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並將相關資料和採訪提綱發給了該出版社。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已經將此轉給中學語文編輯室的老師,會盡快回應劉林源先生。
學者
“其研究志誠令人感佩”
石家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博士高瑩說:“劉林源先生針對新舊選本中《木蘭詩》的文字差異產生質疑,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他的研究志誠令人感佩。”
高瑩介紹,面對古今文學經典,不同時代的不同編者各有其規則和理念。圍繞《木蘭詩》,屬於教科書性質的課本,和早年葉聖陶的《文學》選本出現了文字差池。當前流行的“願馳千裡足”之說,應該源自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這部樂府詩總集首次完整收錄此詩,是一種“完本”生態﹔而“願借明駝千裡足”乃出於晚唐段成式所編《酉陽雜俎》,這部筆記行文中僅摘選此句,或為“殘句”生態。由於《木蘭詩》是世代累積而定型,其成文是一個動態性過程。相關文獻的缺失,使得兩種不同的表述,難以遽分早晚。“千裡足”是馬還是駝,讀者因此爭議不下。
相比中原內地,西北邊塞駱駝確實多出,但不能因此掩抑駿馬的存在。北朝民歌《李波小妹歌》中“褰群逐馬如卷蓬”可以為例,《木蘭詩》本身也有“東市買駿馬”的內証。同時,“明駝”,今人一般依據《酉陽雜俎》,《木蘭詩》中有“明駝”之說或者始自唐人。但是,南朝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早於《酉陽雜俎》,《樂府詩集》源自《古今樂錄》,“願馳千裡足”早出的概率更大。
即便“明駝”之說早出,甚或早於唐宋,教材選擇“願馳千裡足”也不為過。回到《木蘭詩》現場,詩中主要是圍繞出征、思親、征戰、賞賜、返鄉來寫。至於在動態性的成文過程中,回鄉坐騎究竟是馬還是駝,因文本多變而難以指明。問題是,無論字面如何,即便是“願馳千裡足”,對塑造木蘭和欣賞詩意並無重大影響。
如何科學審慎地看待相關問題,值得繼續商榷。首先,文史互証,隻能作為一種研究手段,正視《木蘭詩》成文的動態性,“明駝”與北朝文化聯系的討論須適可而止,不可偏執一端。“願馳千裡足”是一種后出的簡化做法,尚難遽然斷定。如果一時難下結論,依據學術規則可以暫付闕如。此外,與“殘句”相較,今日教材採擷《樂府詩集》中的“完本”《木蘭詩》,作為通行版本,完全合乎情理。況且,“願馳千裡足,送兒還故鄉”,前后五言、流暢明快,動態化的《木蘭詩》本已打上后世或者唐人潤色的印記了。
由此文引申開去,古代詩文經典往往存在諸多類似疑問。諸如“床前明月光”,“床”,有胡床、井床、睡榻等意,各有講通之處,似乎傳統注解或者唯一注解遭遇了沖擊。這裡的碰撞,實質是在原生態訓詁與會意式欣賞之間產生。隨著詩歌的歷史性傳播,讀者可以探究某一字眼的意義指向,但對詩歌的欣賞感動又不會拘泥於字面。也即,字眼的訓詁有其歷史性,注解可以適當做出辨析,即如“床”的解答有所分歧,對讀詩卻不產生實質性障礙,因為詩意不在字面。望月思鄉是普遍而恆久的美好情感,這才是《靜夜思》的“詩心”所在。又如,歷史上圍繞“千裡鶯啼綠映紅”引發的爭議,已經偃旗息鼓﹔唐人邊塞詩中,方位、距離與實際不符的情形也為數不少,學者高步瀛曾論王昌齡《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雲“破樓蘭不必至青海,此不過詩人極言之耳。”(《唐宋詩舉要》)因此,讀詩不可拘泥坐實,如能解讀“雪裡芭蕉”式的藝術思維,方能領悟藝術創作規律和客觀真實之間的距離美。(文/記者 孟醒石 圖/劉林源 提供)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