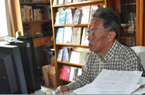《推拿》是一向以小眾文藝情色電影見長的婁燁導演首部得以在主流院線上映的作品,能夠公映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這部影片在剛剛落幕的台灣金馬獎上備受肯定﹔另外,就是它把目光對准了相對弱勢的社會群體——盲人,這樣的人文關懷主題為其博得了加分。然而看過之后才發現,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藝術家的品位與取向,婁燁依然沒有脫離開他最熱衷也最擅長表現的東西。所謂人文關懷,最終成了情欲這瓶老酒外包裹的一個虛假商標而已。
誠然,因為身體的不健全,盲人朋友在婚戀方面會遭遇到更多的挫折,要經歷更長久的等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會急切到無法自控的程度,以至於在數位朋友甚至是人家的男友還在場的情況下,就對剛認識沒多久的女子上下其手死纏不放。愛情的確沒有道理可言,它可能會在一瞬間就生根滋長,不管是一見鐘情還是盲人的這種“一聞鐘情”,都是完全合於常理的。不合理的地方在於,即便是被一觸即發的愛情沖昏了頭,人們也該懂得掌握表達的分寸與場合,不至於這般不管不顧。盲人朋友的身體有缺憾,可他們的頭腦是正常的,這樣如癲似狂的情節於他們來講根本就是一種丑化。
總結看來,電影《推拿》的主創人員並沒有站在與盲人朋友平等相待的立場上,全片一直都在全力渲染的是:“你看盲人多可憐啊!他們多需要愛啊!”唯一能夠表達出這個特殊群體真實心理和生存現狀的是片中的兩段旁白,即盲人視普通人如普通人視鬼神一樣敬而遠之,還有他們更明白什麼是命運。這兩段話既有道理又有文採,還算體現出了一部人文作品所應有的高度,但功勞也是屬於原著作者畢飛宇的。
正如某位網友的評論:“真不知他們到底是在關注弱勢群體,還是在消費弱勢群體。”沒有真誠的接近,沒有發自內心的觸動,只是從獵奇和居高臨下的角度去看待盲人群體,自以為是地把他們的渴望、痛苦加以夸張和放大,包裝成赤裸裸的露點以及血淋淋的自殺、自殘。這樣的人文關懷,實在是要打折扣的。文/本報記者 崔巍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