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阿維拉的聖特蕾薩臉像(樣稿) |
 |
|
聖依納爵的榮耀(樣稿) |
 |
|
聖壇經文牌 |
 |
|
青年男子肖像(油畫) |
文物的樣貌和其背后豐厚的內涵,蘊含著歷史的強音。由此,中國和意大利雙方合辦的“佛羅倫薩與文藝復興:名家名作”與“羅馬與巴洛克藝術”展,先后做客中國國家博物館,奏響了意大利藝術史上的重要兩部曲——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引發中國觀眾的探知欲:15世紀至17世紀佛羅倫薩與羅馬為何相繼成為歐洲的藝術中心?巴洛克藝術和文藝復興又有著怎樣的聯系?展期至明年2月28日的“羅馬與巴洛克藝術”,以來自意大利10余家著名收藏機構的50件(套)17世紀羅馬的繪畫、雕塑和工藝品,在卡拉奇、卡拉瓦喬、貝尼尼等耳熟能詳的藝術大師的作品牽引下,在歷史與藝術的交織中,生動演繹了17世紀一座城、一段歷史與一個盛大的藝術圖景之間的故事,將觀眾的視線推向了歷史的深處。
求變之風
羅馬,一個有歷史分量的名字。它是古羅馬帝國的發祥地、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藝術的中心地之一,被羅馬人驕傲地稱為“永恆之城”,又被世人譽為“萬城之城”,還因有著像羅馬競技場、萬神殿等宏偉壯觀的建筑,以及豐富的雕塑、裝飾公共空間的鑲嵌畫等,被喻為全球最大的“露天歷史博物館”。
如果說,去年的“佛羅倫薩與文藝復興”展,向觀眾展示了文藝復興時期在達·芬奇、米開朗基羅以及拉斐爾等藝術大師的引領下,拭去了神性光芒而萌生人文精神的藝術,那麼今年的“羅馬與巴洛克藝術”展,則使人感受到一種從自然現實到矯飾豪奢的情感變化,在這裡,藝術與歷史的發展脈絡再一次聚合。
16世紀末的佛羅倫薩和羅馬等地,隨著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大師的相繼去世,本來就對他們望而卻步的后來者從一味模仿走向了“矯飾主義”,從對崇高、理性、和諧的藝術追求轉向了對奇巧技法的關注,使得藝術再度失去了生氣與活力。
阿尼巴·卡拉奇和卡拉瓦喬——羅馬兩個“志同道不合”的藝術家,最先點燃了創新之火:前者強調對前輩藝術大師的繼承,推崇理想美,是向傳統回望﹔后者則強調回到真實的現實感受,是向藝術創新張望,均對羅馬乃至歐洲藝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或許也是展覽將卡拉奇和卡拉瓦喬作品放在展廳入口的原因——他們的藝術既是此次展覽的先導,更是17世紀羅馬藝術變革的先聲。
卡拉奇三兄弟創建了歐洲最早的美術學院——波倫亞學院。它開啟了學院派教育的新方式,引導繪畫遠離矯飾之風,回歸所謂的正統,既繼承著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原則,追求和諧、庄重、理想之美,又強調素描和自然表現。此次展出的卡拉奇《青年男子肖像》便是其藝術主張的生動體現,細致的面部刻畫,傳遞著朴實、真摯的人物情感。卡拉瓦喬的藝術則是對文藝復興時期理想化的、安靜平衡並富有理性的藝術精神的反叛,他直接轉向對對象的物理真實和畫家、畫面對象心理真實的刻畫,不回避對丑的表現,如在《施洗約翰》中,卡拉瓦喬將宗教與神話內容移植到了平民世界的生活中,並以人物運動和強烈的明暗對比使畫面充滿戲劇性。
卡拉奇和卡拉瓦喬對當時畫壇的影響,在展覽展出的與兩位大師藝術相關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如簡·德·蒙佩爾的《大自然中的東方游人》等,有著理想式的風景,並表現了人在自然中的活動﹔阿特米西亞·簡蒂萊斯基的《彈魯特琴的聖切奇莉亞》等,有著現實人物的身形、服飾和情感等。他們的作品,既有受科學影響而形成的嚴謹的結構、戲劇化的場面以及精准的透視等,也顯現著藝術家個體審美的覺醒。這種覺醒,在16世紀末的羅馬畫壇鼓蕩起一股創新之風,藝術吸收了文學、戲劇、音樂等領域裡的一些因素和想象,以一種激情打破了理性的寧靜與和諧,不僅成就了羅馬多元的藝術風格,也為17世紀巴洛克藝術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
奢華之象
如果說,以卡拉奇和卡拉瓦喬為核心建構起的繪畫變革是藝術發展的必然,那麼展覽第二、三板塊呈現出的巴洛克風格則是歷史和藝術共同發展的結果,由此成就了它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地位。
“巴洛克”一詞意為“不規則的珍珠”,有古怪之喻,原是對17世紀一種有違文藝復興精神的藝術風格的貶稱,后來逐漸被社會認可。它在歐洲的流行是以羅馬天主教會為主的貴族鼓勵與贊助藝術創作的結果。贊助一直是西方藝術發展的重要動力,並使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為贊助者服務的色彩。此次展覽所展出的巴洛克雕塑和繪畫大多也是為教堂、教皇和貴族而作。
“巴洛克”之所以產生於羅馬,一方面是因為航海發現新大陸后導致商業中心轉移,資本、權利擴張,加上時局動蕩,商品經濟嚴重受阻,導致文藝復興時期建立起的民主勢力減弱、封建貴族勢力重新抬頭,天主教再次登上歷史舞台,並開始利用一種帶有威懾力量的崇高美和華麗美來彰顯其絕對權威和地位﹔另一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說”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精神解放了人的想象力和思想。於是,在16世紀末就初露端倪的巴洛克藝術在教會的推助下,演化為一種更具普遍意義的時代文化。
動蕩不定的時局以及科學証明的宇宙無限空間感,孕育出了“充滿矛盾統一的緊張感、無限擴張的運動感”的巴洛克藝術。在展覽的雕塑、繪畫中,不僅能夠感受到曲線運用所帶來的運動感,以人物關系或運動營造的緊張而又充滿張力的畫面感,以及畫家試圖通過對光的大膽運用和透視效果表達出的空間感等﹔也能看到理性與神秘、貧民對貴族君王的崇拜與資產階級對個人主義的信仰、宗教的正統性與自由思想的種種對立等,它們賦予巴洛克藝術世俗化的享樂主義色彩,同時呈現出繁復夸飾、富麗堂皇、氣勢宏大的藝術風格。
這種藝術風格和其所蘊含的激情為國王、教皇、君主以及富商所喜愛,以彰顯自己的財富和榮譽,並蔓延到宗教題材、宗教建筑裝飾、宮廷裝飾等巴洛克藝術的創作主題上,如《聖壇經文牌》《聖依納爵的榮耀》(樣稿)等,而且畫面的風格和人物形象都充滿了世俗欲望和裝飾意味,如《烏爾班八世的頌贊》(樣稿)中豪華氣派的場面,《聖費德裡科殉道》中衣著華麗的人物等,畫裡畫外流露著奢華的氣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宗教應有的神聖,而多了奢侈、浮夸的世俗感和感官愉悅。
豪奢並不是藝術和生活的終極目標,所以,作為一種時代的藝術,巴洛克雖然在反對僵化的古典藝術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藝術格調、表達世俗情趣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並對城市建筑、廣場、家具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產生了影響,一度在歐洲廣泛流行,但是自誕生之日起,便聚訟紛紜、毀譽交加。
至今,“巴洛克”依然因其富麗堂皇的審美表達為不少人所喜愛,甚至新建的不少歐式建筑以及廣為銷售的歐式家具等,都可以看到巴洛克藝術的影子,但少有人留意,富麗堂皇之外,那奔放的曲線中流淌著的藝術情感。藝術的最終目的是精神的安寧和愉悅,幸福快樂也不在於形式,而是除卻表面浮華后的精神富足,也正是這種精神上的契合性,造就了藝術與生活之間亙古綿延的關系,不斷創造著人類璀璨的文明。因此,今天重溫“巴洛克”的意義,不隻讓我們看到了羅馬這座昔日帝國之城在剛柔相濟中演繹出的輝煌歲月,更重要的是在其鏡像中能夠重新反思藝術的根本價值與意義所在。
《 人民日報 》( 2014年12月14日 12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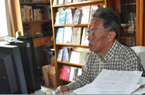














 傾聽12.13幸存者的心聲
傾聽12.13幸存者的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