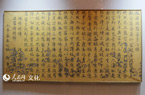酒與詩文,二者密不可分
唐代“竹溪六逸”,指開元末年,李白與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六人,結隱在泰安府(今山東泰安)徂徠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縱酒酣歌,以酒會友,以文會友。
唐代詩人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詩,描寫賀知章、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態,勾劃他們豪放不拘的性情。詩句“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從徂徠山下走出來的本色。不過,賀知章等八人並無一起聚集宴飲,只是先后在長安呆過而已。
看來,吟詩覓句,成為飲酒玩情調的一種文字游戲,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訴求。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錄有一段逸事:明代蘇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學工文,頗攻詩。其在吳中舊族王氏家中教書時,一天,朱老夫子與主人晚酌之后,獨在庭中,適見月上,靈感一動,吟得詩句:“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吟畢,喜極而狂,拍門大叫,連呼主人起來。
主人聽罷詩句,亦擊節贊賞,當即令人取酒,兩人重又對酌,直至興盡而罷。次日,又遍請吳中善詩者來欣賞佳句,一連數日擺酒戲樂,成為一時盛事。
在文人飲酒過程中,連酒具也成為玩情調的一種方式。
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魏正始年間,每遇三伏之際,鄭懿常帶著賓客、幕僚在歷城(今山東濟南)使君林避暑。他們連莖摘取大蓮葉,以簪刺葉,令與莖柄相通。在蓮葉上盛酒三升,“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杯”。據稱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統等四十一人,在山陰蘭亭(今浙江紹興縣西南蘭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禮。他們宴集於環曲的水渠旁,置酒杯於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當即取飲,名為“流觴曲水”。席間每人賦詩一首,合為一集,請王羲之為詩集作序。序中王羲之寫道:“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流觴曲水,一觴一詠,難道不是在玩情調嗎?
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