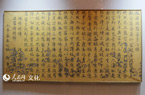元代貢奎《雲林遺事》載,元代楊維禎善詩文,工書法,因文風格奇詭,被譏為“文妖”。晚年居鬆江,耽好聲色,縱恣詩酒。一天,與倪瓚會飲於友人家,楊維禎竟把陪侍妓女的鞋脫下來,置酒杯於鞋中,讓座上客人傳飲,名曰“鞋杯”。畫家倪瓚素有潔癖,一見“鞋杯”,不覺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文人飲酒玩情調,一味追求新奇,有的干脆自釀自飲。比如,宋代黃庭堅、陸游先后賦詩稱贊自釀的“醇碧酒”。尤其是蘇東坡,在北宋紹聖元年(1094)被貶惠州時,其《桂酒頌》詩的敘曰:“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另一首詩《新釀桂酒》中,描述自釀的詩句:“搗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喝上自釀的桂酒,悠然自得的情調躍然紙上。
宋代張舜民《畫墁錄》載有五種飲酒方式:“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宋代蘇舜欽、石延年均好酒能詩,有狂名。所謂鬼飲者,不燃燭火,摸黑而飲﹔了飲者,每飲一次必挽歌哭泣﹔囚飲者,圍坐一處,僅露頭而飲﹔鱉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露出頭來,飲完又縮回去﹔鶴飲者,飲一杯后上樹,再下樹而飲。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亦錄有“五飲”,略有不同。石延年“每與客痛飲,露發跣足著械而坐”。他不僅露發光腳,還要自戴器械,謂之囚飲。坐在樹梢飲酒,謂之巢飲。用干草束裹其身,露出頭來飲酒,謂之鱉飲。其余依前無異。
據明代曹臣《舌華錄》載,東漢皇甫嵩,少好《詩》、《書》。其認為“凡醉各有所宜”。“醉花”適宜白天,薰染其明艷﹔“醉雪”適宜黑夜,明晰其思緒﹔“醉得意”適宜歌唱,顯示其應和﹔“醉將離”適宜擊缽,以壯其行色﹔“醉文人”適宜謹慎禮節,害怕其輕侮﹔“醉俊人”即才智特出的人醉酒,適宜增加杯盆等盛具,添加旗幟,以助其威勢﹔“醉樓”適宜暑天,憑依其清涼﹔“醉水”適宜秋天,浮現其爽朗。“此皆審其宜,考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上述八醉八宜,幾近醉酒玩情調的“大全”。
此外,南朝宋的劉義慶《世說新語》錄有王恭的一句大實話:“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也算是一種情調。當然,到了爛醉如泥,嘔吐滿地的時候,也就無個性可言,亦玩不出情調了。返回騰訊網首頁>>
| 上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