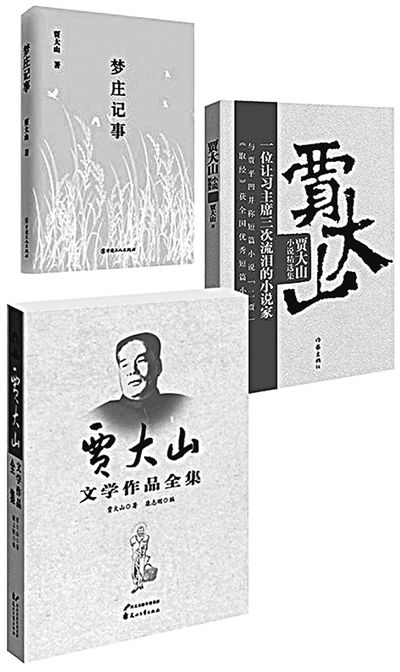
近來,已故作家賈大山頗受關注。他生前沒出過一本書,如今他的作品全集和選本卻都十分暢銷。
文壇緣何重新發現了賈大山?他的作品,有著什麼樣的風格特征與藝術價值?他的為人和為文,又能給今天的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對於這些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試圖給出答案。
——編者
習近平同志寫於1998年的文章《憶大山》,今天讀來仍令人感動不已。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心與心的赤誠相對,是人格對人格的欣賞,是對人才的由衷尊重,令人想到了高山流水酬知音般的高尚境界。反復通讀此文,不由眼熱心酸。
習近平同志評價賈大山的話,顯示了他知人論世的超卓眼光。賈大山有著洞察社會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獨特視角,他率真善良、才華橫溢、析理透徹。如何從人品到文品綜合考量和發現賈大山的價值,令人深思。
必須看到,賈大山堅持為人民寫作的實踐和精神,在今天仍給我們以啟示。他的短篇小說,在今天仍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如果沒有這個前提,賈大山是難以引起如此廣泛關注的。賈大山曾說,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寫自己熟悉的生活、自己熟悉的人物更有把握。他極其重視深入生活。他是以寫實為主的現實主義作家,但如果有誰因此認為他在藝術上不講究,那就大錯特錯了。早在1989年作家鐵凝就說過,賈大山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有樂觀的辛酸、優美的丑陋、詭譎的幽默、愚鈍的聰慧、冥頑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溫馨。由於他堅持將真善美作為藝術的永恆價值,他的不少作品便如水落而石出,在事物的表象之下,保持著鮮亮而深邃的對生活、人生的洞見和展示。在我看來,賈大山小說的本真的美是存在的、深藏的,任何表面的價值和時髦的風尚都掠不去它,藝術並不與時間同步。
在賈大山的創作中,罕有荒誕、變形、魔幻等繁復的手法,而是多以素朴、明快、簡潔的面貌,按生活的本來模樣加以呈現,顯露生活自身的美。凡是被橫流的物欲、浮華的世風所眩惑的人們,盡可以到賈大山的作品裡去恢復一下感官的清新,結識幾個未遭涂污的靈魂。例如《花市》,主人公是個叫蔣小玉的姑娘,她上市賣花而購者甚眾,說明“原來鄉下人除了吃飯穿衣,他們的生活中也是需要一點花香的”。作者敏銳地察覺到,買花人並不都懂得欣賞花,其中仍有個別的低俗者,在敗壞花香四溢的空氣。蔣小玉沒有把美麗的令箭荷花賣給那個濁氣熏人的“干部”,卻廉價地賣給了那個老農,引發了一片會心而開懷的笑聲。作品不但寫出了姑娘花一樣美好的心靈,也映照出人心的轉移、世道的變換。
應該看到,從《取經》到《夢庄紀事》系列,賈大山突破了原先較狹窄的觀念束縛,完成了創作上的一次飛躍和蛻變。距離拉開了,不再滿足於“近視”地評價生活,給人以“后退一步,海闊天空”之感。這個系列的作品,格調深沉,韻味悠長,不露聲色,於平易中顯深刻,於素朴中見濃度。它們大多是對往事的追憶,經過了反復含詠、體味和咀嚼,是作家心靈中的財富。與作家原先恪守的“忠實再現”不同,這組作品具有“再現中的表現,寫實中的寫意”的特色。例如《花生》就深受好評。人們大多是從批判和控訴極“左”路線的角度著眼的,震撼於為一粒花生而死的小姑娘,震撼於生命的尊嚴不如一粒花生。其實,小姑娘的父親,那個永遠把小姑娘扛在肩上的生產隊長也很值得注意。他一聽到要動用花生,就牙疼似的吸氣,反復強調要保証給國庫上繳,申明“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他最心愛的小姑娘偷吃花生,被他猛擊一掌,花生卡在喉嚨,死了。試問,這是個冷酷至極的人嗎?當然不是。這是一個極深刻的精神悲劇。
《夢庄紀事》中的那個“我”,也不再是單純的故事敘述人,而是與農民共思考、共反省的角色,體現了作家主體意識的強化,還含有研究民族性格的指向。例如在《俊姑娘》裡,俊姑娘是個漂亮的女知青,剛到夢庄,村人視為珍寶,還說她的俊氣能降瘋魔。時日一長,她的形象就不佳了,長得漂亮成了罪惡,她愛唱歌、愛寫信,全成了不可饒恕的缺點。由於她比別人多了個“漂亮”,在其他方面都得比別人少點什麼才行,直到她因勞動被砸傷了腿,處境才有所好轉。這不是很耐人尋味嗎?與這種無情的解剖相聯系的,是作品抒情性的強化。那不是膚淺的歌吟,而是能進入人物心靈深層的、帶點憂郁色彩的感發。《干姐》就具有這樣的氣質。干姐是個自己無緣受到文化教育卻艷羨和尊重文化人的鄉村女性,她潑辣、粗野,卻反對“我”變得粗俗。由於“我”胡琴拉得好,她要“我”認她為干姐,覺得自身也有了某種價值,引以為豪。
在今天,賈大山給我們的另一重要啟示是:堅持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致力於對傳統的更新又不失傳統的精髓,反對機械化生產或有數量無質量、有高原無高峰的“以創作豐富自娛”。賈大山強調厚積薄發,博而能一,他說,假如用可以蓋一座樓房的材料蓋幾間平房,哪兒做檁,哪兒做梁,任你挑,那平房一定蓋得好﹔反之,那樓房也肯定蓋不成,隻能東拼西湊了。這話既朴素又深刻。別人改稿可能越改越長,賈大山卻是越改越短。他向戲曲和民間文藝汲取營養,也向《聊齋》取經。由於寫作體裁的不同,我們也許不能做到他的惜墨如金,但提高審美的純度,錘煉漢語的美質,正是今天純文學的生存之道。
賈大山是一名隻寫短篇小說的作家,他對短篇文體的貢獻值得挖掘。他有著在藝術上“世故到極點的天真”,一貫重視磨礪自己的“白描”功夫,即去粉飾、勿賣弄、有真意的寫法。他經常挂在嘴邊的是“下筆不靈看飛燕,行文無序看花開”,極重視靈感的獲得,向大自然和傳統文化學習藝術技巧。他的作品猶如一個衣著朴素、式樣合體、不施鉛華、身材健美的農家少女。賈大山是可以背誦自己的小說的,可見他的用心之深、打磨之精。“簡潔”,曾是短篇創作中備受推崇的品格,賈大山因“簡潔”而獨樹一幟。可是現在的短篇創作中,卻有一種繁縟和冗長之風——缺少提煉的故事,沉悶無趣的敘事,無節制的長句子,正在破壞短篇的藝術特質。回頭看賈大山的短篇,在今天不也是難能可貴的嗎?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