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都故城文物保護碑

△古城北城門的殘城牆
在昌平區的沙河鎮域,有一座距離北京最近的明代古城。古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重的功能仿佛在向每一位來訪者表明著她不同於一般古城的身份。
出於對這座古城的神往,1984年以來我曾近百次造訪過這座古城並在2010年以一部《風雨滄桑鞏華城》表明過對這座古城的無限情思。今年夏初,我故地重游再次來到這座古城中,躍入眼帘的雖然多是搬遷后的殘牆舊屋,但也從搶修文物的工作現場感受到了新的希望正在孕育之中。
“宮殿連雲起,城樓入漢低”
北京附近的古城,一般多與駐軍防護關系密切,可鞏華城除了這項功能之外,還有兩項其他古城不具備的特殊功能,這就是:皇家御用。不光與皇家的活人打交道,還要與皇家的死人打交道。
“宮殿連雲起,城樓入漢低。”
鞏華城的前身,曾是大明皇帝朱棣在永樂十九年建造的一座行宮,主要用於皇帝北征、建陵路途歇腳的一個地方。后來朱棣把他的陵址定在了昌平的黃土山一帶(今十三陵陵址),這裡也就成了皇家謁陵、送葬的必停之地。
正統初年的大水患把行宮沖毀以后,曾經在景泰和天順年間有過兩次重修的記載,但由於各種原因,到嘉靖之前,只是在行宮之地臨時搭帳供皇帝往返歇息之用。
嘉靖十七年五月開始,在重修沙河行宮的基礎上在行宮之外圍筑沙河城,五年之后世宗皇帝親命“鞏華城”。
古籍記載:為建造鞏華城,明廷撥款白銀200萬兩,派重臣督建,確定行宮和環城的具體方位和尺碼,行宮建於城內正中偏南,為防水患地基加高至二丈以上。鞏華城城牆高為三丈五尺,周長四公裡共設3602個垛口,城角四座角樓,南北兩城門為鑾駕出入之門故各開三門,南城樓尤為壯觀,與北京紫禁城的午門建筑規格相同(“制如午門”)。南北大門各設三座千斤閘,東西各一千斤閘,四門之外均建瓮城。行宮則圍牆飾紅,黃色琉璃瓦封頂宮內三路而建,這裡隻說中路有龍蹕門(行宮正門)再有龍蹕殿(行宮正殿),制如十三陵長陵內的裬恩殿……
鞏華城之重要僅從鞏華城南北兩個瓮城和東西南三個門的漢白玉門額題字上就可見一斑:南門正門之上“鞏華城”有鞏守京華之意﹔東門之上為“鎮遼門”起“鎮闥東遼”之意﹔西門之上“威漠門”有“威揚大漠”之意﹔北門瓮城之上為“展思門”,取展懷皇恩之意。這幾個門額題字為“館閣體”,史書記載均為禮部尚書嚴嵩所寫。
通過一座古城幾個門額題名之意可以看到雖然鞏華城城池的面積不大,但是皇家卻對她的功能寄予著重托,這也許就是鞏華城“城小位尊”的重要之處吧!
在明代,鞏華城的南北兩城門為皇家車駕出入之門,每年皇家春秋兩大祭或送帝后靈柩到行宮停靈住宿,皇家進出南北正門的中門,隨護大臣按文東武西的儀規進出中門兩邊的左右掖門。軍卒官兵隻准從東西兩城門進出。鞏華城內在明萬歷年以前為禁地,不准居民百姓入城居住。
鞏華城浚池瓮門設備齊全、固若金湯,城外南北沙河相夾,船泊片片揚帆點點,北沙河上有今天依然發揮著作用的北京名橋“朝宗橋”﹔南沙河則留下了著名的“安濟春流”佳話,平添了鞏華城之美韻。據古籍記載:當時南沙河河寬水深,西銜遠山,煙波浩渺,九孔安濟石橋橫臥於碧波之上﹔鞏華城雄踞北岸,城樓巍峨,牆堞庄嚴,泊岸上人來人往,搬糧運貨,商旅匆匆,駝鈴聲聲,一片繁忙景致。常見岸邊蘆葦深處,釣翁端坐、舉竿垂釣,兩岸稻香荷艷風輕水靜,魚翔水底鷗鳥低飛,真乃一派江南水鄉秀麗的景象……
“風雨滄桑后,碧空見虹霓”
時至如今,鞏華城已經走過了四百七十余個年頭,曾經的宏偉歷經滄桑之后已是滿目瘡痍,殘存的瓮城和城門之上的石刻依然仿佛在向人們訴說著過往的歷史。怎樣利用鞏華城厚重的文化底蘊,再創鞏華城今日輝煌已經成為政府、商界、百姓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風雨滄桑后,碧空見虹霓。”
我們已經欣喜地看到,各級政府和文物工作者已經把鞏華城的搶救、保護、管理、利用放在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昌平區委、區政府正在把鞏華城與明十三陵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的建設和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北京市政府也已經把鞏華城的保護利用列入北京TBD建設規劃之中,日前所有關於鞏華城舊城改造的計劃和建設都與舊城內歷史街區的搶救保護管理利用融為一體,應該說鞏華城煥發青春的日子已經進入了倒計時,前五百年的滄桑與五百年后的輝煌將在這裡實現傳承和發展。
在緊鄰鞏華城南門的一個小區內,我見到了暫居這裡的退休女職工譚淑華和她的幾位老鄰居。她熱情地把我讓進小院,指著她們親手制作的鞏華城全貌沙盤讓我評點。原來在2013年沙河鎮舉辦的“大講堂”聽過我主講的《風雨滄桑鞏華城》之后,譚淑華憑借著“年輕時積攢的藝術功底”和“大講堂”上的筆記硬是帶著幾位鄰居、老工友用了200多個日日夜夜,精心地制成了這個沙盤……
正午的陽光,已經讓我感到了夏日酷暑,鞏華人的情懷更讓我的心頭熾熱萬分。無需再多的言語,鞏華城情結正在這裡延伸,鞏華城的歷史文化也正在延伸中發揚光大!楊廣文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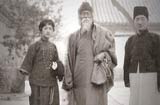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