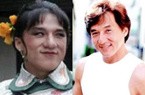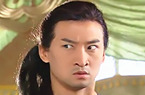徐崢、田曉鵬、韓延、吳京、寧浩……這些名字也許沒有明星熱門,但如果與《港囧》《大聖歸來》《滾蛋吧!腫瘤君》《戰狼》《心花路放》等電影聯系起來,他們就是當之無愧的流行文化操盤手。
數據顯示,從2012年到2014年,58部票房過億元的電影中,有26部都是70后新生代導演的作品﹔2015年7月前上映的有票房可查的95部電影中,新生代導演的作品65部,佔比68%,票房佔比48%,甚至還有80后的導演創造了20%的電影票房份額。
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主辦的“中國電影新力量”論壇近日在京舉行,這些70后、80后的青年電影人,聊起了他們當導演的那些事兒。或許,年齡不是問題,中國電影的新力量已經改變了中國電影。
徐崢:有了“囧”系列,為什麼還要看《雷雨》
“其實,我是一個演員。”徐崢的演講是這樣開場的。從小學三年級就被拎出來演戲,一直到大學畢業演的都是舞台劇,這讓他有著直面觀眾的經驗,“觀眾直接在下面給你反饋,笑了、哭了、感動了”。
徐崢回憶,小時候到老式電影院裡去看《佐羅》《少林寺》,所有觀眾擠在一起,好像整個影廳都有巨大的能量。“事實上是因為這個電影滿足了觀眾的一些需求。等到我自己拍電影,我也一直有一個觀念,一部電影要到觀眾看了之后才算完成。”徐崢說。
晉級成為導演后,徐崢有個習慣,提前到電影院待著,觀察觀眾,看他們排隊買票、觀影的一系列行為。“我想知道,作為一個觀眾,他下了班匆匆坐了各種交通工具,跟朋友約好來看這樣一部電影。為什麼選我這部?我又要拍什麼電影給他們看?”
所以,電影人面臨兩個問題,一是觀眾要看什麼,二是自己想拍什麼。徐崢覺得,導演有義務和責任和觀眾共同來做一些探討。自己的每一部電影上映后,徐崢都會看完幾乎所有的影評,不管好評差評,他都覺得是觀眾參與作品的一部分。
拍了票房大賣的《泰囧》《港囧》,有人調侃,下一部要不要去荷蘭拍《荷囧》?徐崢用一個故事回答了這個問題。
徐崢碰到過一名專拍莎士比亞戲劇的德國導演。徐崢問:“這個時代,為什麼觀眾還要看莎士比亞?就像中國學表演的人,為什麼一定還要排練《雷雨》?”導演回答:“因為經典中的每一個段落,都包含了很多人類共通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劇中主人公身上,而且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而且關鍵劇作沒有給一個標准答案,引發的是觀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田曉鵬:好故事沒有捷徑,死磕
作為一名標准的70后,田曉鵬小時候正趕上電視機進家門,動畫片成為童年最美好的記憶。看了日本的、美國的,但最打動他的還是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片子,“后來想想,大概是老外的東西再怎麼精良,也打不到我心裡”。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田曉鵬偶然瞄到一個三維畫面的電視廣告,特別驚訝為什麼廣告裡的虛擬人物能夠栩栩如生。媽媽告訴他“這是計算機做的”,這讓田曉鵬當即覺得,長大了我要干這個。
20年后,一部《大聖歸來》讓田曉鵬一夜成名,盡管這背后是8年的醞釀和3年的拍攝。“電影是一個特別神奇的東西。很多網友給我私信,表達了一個共同的觀點:你這個片子對我影響很大。還有孩子問我,我打算高考報動畫專業,我需要注意什麼。”田曉鵬這一刻覺得,本來是自己玩兒的事,其實責任很大。
曾經以為迪斯尼能做出行銷全球的動畫一定是因為它擁有完整的電影工業體系,但不久前參加了一個與迪斯尼的交流活動后,田曉鵬發現,“死磕”才是迪斯尼的王道,“光一個故事就可以寫一到三年”。“好故事是沒有捷徑的,就要踏踏實實做。”
現在,全世界的動畫幾乎是美式和日式兩家獨大,但田曉鵬在做《大聖歸來》時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融合這兩種模式取其長處,同時加上中國的哲學美學。“所以《大聖歸來》裡有一點點實驗性的東西,也有觀眾告訴我,這正是片子的亮點。”田曉鵬透露,他下一部拍攝的科幻片還將繼續這樣的嘗試。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左衡評價,田曉鵬是“非古典的古典”。《大聖歸來》橫空出世后,上一輩人說這是對古典的顛覆,而看了后發現,片子還是有古典的情結,包括對中國繪畫中非常有趣的元素的使用。
吳京:愛國主義也能有“燃點”
曾經的演員吳京,用7年時間完成了一部自己的心願之作《戰狼》,成為導演吳京。《戰狼》講述的是一場中外邊境戰爭中中國特種兵部隊的故事。有影評說,《戰狼》是小鎮青年的勝利,是他們撐起了這部現代戰爭題材電影的票房。吳京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嘲諷,因為“再優秀的電影也不應該只是討好精英階層,而應該讓全民都有‘燃點’。”
在吳京看來,“電影以人民為創作導向”這句話特別務實,“沒有人民看,你的票房從哪兒來”,同時也要進行一定良性引導。吳京說:“現在屏幕上的中國男人太軟,需要有陽剛、硬朗的形象,《戰狼》就是中國爺們兒內心情感的宣泄。”
吳京說:“曾經我們說到愛國主義,會熱血沸騰,后來卻覺得就是一句口號。以至於我拍這個題材的電影時,受到了各種白眼和掣肘。但《戰狼》之后,這個框框被打破,証明愛國主義是有情懷有市場的,主旋律題材能被大眾接受。”
吳京認為,如果說《鋼鐵俠》是美國在輸出他的英雄主義,那中國的英雄主義隻要有一個好的故事外殼,一樣可以向世界輸出,而這個外殼就是國際市場對中國電影接受度最高的題材——動作電影——這也正是吳京做演員時的老本行。
吳京覺得,中國的動作電影並不缺特效,缺的是劇情。動作電影從李小龍、李連杰、成龍發展至今,已經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但類別一直沒有深度開發,甚至轉而講求禪意。“其實動作電影是包羅萬象的,將‘動作’這個核心與其他元素結合就會呈現更多的可能性。”吳京舉例,動作和江湖結合就是武俠電影,和警察結合就是警匪電影,和軍事結合就是戰爭電影。“曾經的中國功夫巨星讓世界都知道了中國功夫,現在又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樹立中國標簽、中國風格的動作電影。”吳京說。
專家:新一代電影人成為文化建構的中心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孫向輝介紹,該中心從2015年年初正式啟動“中國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報告”項目,截至目前完成了春節、春季、暑期、國慶四個檔期的調查。綜合觀眾、專家、大數據等三項大指標,報告顯示,春季檔的《戰狼》是一匹黑馬,處於滿意度的高位﹔《大聖歸來》成為年度最受歡迎國產影片,排名第二的分別是《滾蛋吧!腫瘤君》和《捉妖記》。
無論從票房、口碑,還是價值觀的有效傳達,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肯定地說:“新生代導演已經不再是黑馬,而是中國電影的新力量,代表著中國電影發生的巨大改變。”
尹鴻認為,發生改變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新市場、新觀眾的出現,“電影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四五線城市擴散。曾經由大城市白領決定的電影趣味向更廣闊的空間普及,越來越多的小鎮青年有了話語權”﹔第二是互聯網創造的力量,“伴隨互聯網長大的一批人已經成為主力電影觀眾,雙重身份的契合使中國電影比其他國家有著更明顯的互聯網氣質,而電影和互聯網恰恰是中國的文化行業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兩個領域”﹔第三是新電影人的出現,“他們不僅伴隨互聯網長大,也在受教育過程中接受了大量科技教育,對娛樂文化、大眾文化的規律、特性有著非常清醒的認知,將本土化和專業化相結合”。
最能讓尹鴻看到這些電影新力量未來所在的是,他們的電影不僅提供了消費品,還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常識與文化建構。“《滾蛋吧!腫瘤君》《十二公民》《大聖歸來》等電影中傳達的那種向上、勵志、尊重人格獨立和個人選擇的價值觀,恰恰是現代社會所必須的,這也是中國電影最可喜可賀的一點。”尹鴻說,“這一代電影人不僅登上了市場的中心,他們也成為文化建構的中心。”(蔣肖斌)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