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申在戰車前留影 供圖/楊紅軍
田申,著名戲劇家田漢的長子。1924年12月出生。1943年參加遠征軍赴印緬作戰,抗日戰爭勝利后赴晉察冀軍區工作,歷任營、團、師、軍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離休。2012年2月9日在北京辭世。田申經過戰爭的洗禮,從一個襁褓中喪母的孩子,成長為解放軍的一名指揮員。他的胸中涌動著田漢愛國憂民的熱血,他的骨子裡鑄就著人民軍隊的魂魄。
1949年7月,聶榮臻司令員交給華北獨立戰車團代理團長田申一個任務,讓他帶領坦克方隊在開國大典上受閱,准備時間為三個月。田申當即立下軍令狀:一定完成任務!
任務光榮而艱巨。最棘手的問題是,我軍的坦克主要是華北各地戰場上繳獲的戰利品,日式、美式都有,“身經百戰”的坦克都千瘡百孔,大部分“缺胳膊斷腿”的。要湊齊坦克達到開國大典的受閱標准,太難了……田申找到聶榮臻說:“聶司令,你給我的任務,要我三個月能通過天安門,很困難。”聶榮臻說,“不要別的,隻要你這個坦克方隊,通過天安門這一段不要拋錨就行。”
田申認為,閱兵是傳統的軍事儀式,也是展示人民軍隊風貌的重要窗口。戰車方隊必須以最壯觀的形式和姿態受閱。他覺得美式坦克比較小,在天安門廣場上開起來不好看,決定使用日式20噸的中型坦克接受檢閱。按照長安街的寬度,並排三輛,一共十排,再找十輛備用,這樣看著最合適、最氣派。於是,田申帶領團修理連像戰爭年代一樣,集中兵力打修復坦克的攻堅戰,夜以繼日地搶修坦克。坦克主要是發動機要好,然后是履帶的傳動部分要好。當時,他們先找到發動機好的坦克,缺乏零部件,干脆就從廢舊坦克上面拆卸下來,再重新拼湊組裝,群策群力,終於用了一個多月時間,集中全力突擊修復了20多輛坦克。由於戰場上繳獲來的坦克,難免有損傷,所以,田申命令戰士們把這些坦克好好地“打扮”一番,將全團的坦克和裝甲車輛都噴上了偽裝漆,並精心地噴上“八一”軍徽和編號。但是,這種臨時組裝的戰車能不能順利通過天安門,田申心裡沒有底。
根據開國大典閱兵指揮部的要求,受閱的戰車方隊經過天安門時,除團營指揮員坦克敞開頂蓋外,其他坦克均需蓋上頂蓋前進,並保持4輛一排,每排間隔30米,時速15公裡,用8分鐘通過從東三座門至西三座門之間的天安門廣場。現在聽到這個方案,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但當年要達到以上要求,卻相當不容易。
為了出色完成閱兵指揮部交辦的任務,田申從全團挑選出優秀的車長、炮長,一車三個乘員進行編隊集訓,操練地點在復興門外公主墳附近的沙窩一帶。那時的戰車缺乏通訊工具,既沒有電台,也沒有車內通話器,要保持戰車編隊縱橫整齊、協調一致地前進,怎麼辦?田申想了一個辦法:本來開坦克要求人不能露出頭,但是沒辦法,為了能讓戰車方隊達到受閱要求,沒電台,就用人聯絡。他就在最前排右面的坦克上站起來,用腳踩到駕駛員的肩膀上頭,他跟駕駛員規定了腳踩的暗號,比如開快點,腳就往前使勁兒,往左開就左腳蹬一下,踩幾下就停止,踩幾下是前進……這樣,他在最前排右面的坦克上做出動作,指揮他左邊的三輛坦克,后邊的坦克都以前排為基准,前后對正,左右看齊。車長和駕駛員隻能憑借潛望鏡在車內觀察。由於受客觀條件所限,唯有發動指戰員加緊刻苦訓練。
隨著開國大典的臨近,田申和戰友又利用兩個夜晚,組織戰車方隊到天安門廣場實地演練。戰車行進到東三座門時遇到難點:三座門的三個門洞隻能並排通過三輛車,而每排第4輛車則須從東三座門以南繞行,然后迅速加入隊列保持隊形,這需要調整車速和整個方隊的協調照應。他們又反復練了幾遍才解決這個課題。臨接受檢閱之前三個晚上,半夜兩三點,田申帶著受閱團到天安門附近的東華門,就像正式接受檢閱一樣去演練。
10月1日閱兵當天,炮兵方隊之后,就是戰車方隊。在獵獵的八一軍旗指引下,當戰車開到天安門城樓前,田申庄嚴地向毛主席和中央首長致敬。這時,恰巧與天上飛過的空軍方隊同步。天安門廣場上戰車隆隆,方陣齊整,金戈鐵甲,盡顯雄風。蔚藍色的天空中,人民空軍年輕的戰鷹編隊飛過。天上地下,渾然一體,展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之師、威武之師的雄姿。
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戰車方隊順利地通過了天安門廣場。不過在受閱后退場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有一輛車在西華門拋錨了,不過后面那個車的駕駛員很機靈,毫不猶豫地把它頂出去了。半個多世紀以后,田申回憶說:“真危險啊。幸好沒有在天安門城樓前拋錨。不過我也是完成了任務。如果哪天我能開著國產坦克過天安門,那多好啊!”
幾十年來,田申收集了許多歷史資料,經過戰亂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仍然保留了一些老照片、家信以及田漢、郭沫若等人的詩詞手跡。這些家庭檔案和個人檔案彌足珍貴,見証了田申的人生志向與情懷。(北京市檔案局 楊紅軍)
(來源:北京青年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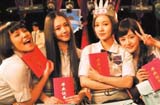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