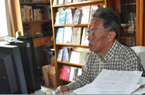《紅高粱》劇照
導讀:正在北京衛視播出的《紅高粱》,收視和口碑均超出了預期。不過,躲不開跟小說、電影的比較,兩相對照,劇版《紅高粱》“問題”還真不少﹔另一個繞不開的是,鄭曉龍的前作《甄嬛傳》也是國產電視劇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宮斗”變“宅斗”,鄭曉龍忍不住反問一句,“難道我們在土地上斗,就是土豆(斗)?”而編劇趙冬苓則坦言,這次對人物的塑造多少受到鄭曉龍導演的《甄嬛傳》影響,從“方正大氣”轉向“三觀不正”,隻為跟觀眾更親近。
編劇趙冬苓:人物塑造受《甄嬛傳》影響
《紅高粱》在北京、東方衛視播出后引起激烈討論。除了電影、電視劇版演員、風格上的比較,劇情上的改編也引發了一些爭議。昨天,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編劇趙冬苓給自己打了85分,“莫言先生非常放任我們去改編,我們是很大膽地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全劇60多萬字一點水都沒有,故事非常緊湊、飽滿。”的確,不同於張藝謀電影版的寫意風格,趙冬苓改編的最大特點就是加入了多條故事線和翔實情節,新增了九兒初戀情人張俊杰、單家大嫂淑賢、縣長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戲人物多達58個,而且個個色彩飽滿、個性飛揚。趙冬苓自解謎底,坦言這次對人物的塑造多少受到鄭曉龍導演的《甄嬛傳》影響,從“方正大氣”轉向“三觀不正”,隻為跟觀眾更親近。
調整思路
創作中要把自己端的東西放下來
《母親母親》、《北方有佳人》、《葉落長安》……趙冬苓過往有著自己的一套女性角色系列,但《紅高粱》中的九兒,卻是她頭一個跳脫了“三觀正確”的叛逆角色,劇中甚至出現了九兒給土匪出主意敲詐自己的父親及其忍無可忍不得不設計對嫂子反擊等情節。趙冬苓向記者坦言,這種全新的創作思路或多或少受到鄭曉龍導演的名作《甄嬛傳》的影響,“《甄嬛傳》裡很多人物都是‘三觀不正’,而我過去寫的女性形象,一般別人評價都是方正大氣。是《甄嬛傳》的人物塑造,讓我體會到觀眾可能更喜歡的是能力、審美和道德水准和我們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點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觀眾隻能膜拜,就不親近了。我開始寫《紅高粱》以后,在創作風格上有了比較大的轉變,把自己端的東西放下來了。”
關系扎實
熙攘的“煙火氣”,是電視劇的創作方向
電影版《紅高粱》場景大多荒涼,十三裡坡和高粱地給人一種空曠感﹔而電視劇裡,九兒生活的高密縣有著熙熙攘攘的煙火氣。關於這樣的差異,趙冬苓強調“煙火氣”對電視劇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電影的篇幅和藝術追求,可能追求那種意象就好,沒必要表現出非常扎實的故事、非常復雜的社會關系,但是我們的電視劇肯定在這方面有要求。”趙冬苓認為,“電影藝術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細地編排故事,表現人物關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現精神,但對電視劇來說遠遠不夠,我們要把人物放在一個很有煙火氣的地方。”導演鄭曉龍與趙冬苓的想法不謀而合,“電影偏陝西,我們這放在山東。陝西是蠻荒之地黃土高坡,山東是非常扎實、生機勃勃、各種復雜的社會元素交融的一個地方。”
為了讓作品更有“人煙味”,電視劇一改電影版的思路,選擇從九兒的女性視角出發,而新創朱豪三、大少奶奶、張俊杰這些角色,不僅豐滿了那個年代的眾生相,也起到了補充九兒的社會關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趙冬苓舉例說道:“為了和九兒的叛逆形成對照,就有了用傳統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
自我要求
就算觀眾不在意,也不能放過“不合理”
接手高人氣作品的改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更何況《紅高粱》這種“諾獎”級別的作品。“改好了會說是莫言作品好,改不好會被罵,”趙冬苓曾為此擔心,但最后還是接了這個本子。
重壓之下,3個多月寫了60萬字的“快手”趙冬苓也曾卡殼。開拍之后,劇本還在不斷修改。談及與導演鄭曉龍的合作,趙冬苓笑言鄭導是一個特別特別較真的人,對情節的合理性十分嚴謹,讓寫作時天馬行空的自己學到不少東西,“我原來第一集就是一開場打更的人發現地上滴血,抬頭發現是前任縣長被吊死了,然后就開始叫‘土匪來了’,滿城雞飛狗跳。我對這個開頭很滿意,但是鄭導認為不合理,說剛打更就雞飛狗跳不可能。我說觀眾不會在意的,但他說不合理。這一點上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文/本報記者 楊文杰
導演鄭曉龍:我確實找不到一個年輕時的姜文
昨天下午,針對《紅高粱》沸沸揚揚的熱播和熱評,導演鄭曉龍接受了北青報記者的採訪。關於這次創作的成敗是非,觀眾評價都免不了小說、電影、《甄嬛傳》這些參照物。鄭曉龍聽多了開始“撓頭”,“老這麼比,其實是個誤區”。他說自己在接下這個“燙手山芋”時,想的只是如何按照電視劇規律將其拍得好看、心動,而今天陷入比較“怪圈”始料未及,但他“不后悔”。
關於改編
電視劇是一點點地表現人物
北青報:電影裡很多橋段是令人津津樂道的,拍成電視劇既不能照搬也不能繞開,您是如何解決這個“坎”的?
鄭曉龍:我覺得《紅高粱》基本上還是遵循原著的,特別是原著的精神,非常重要。顛轎和野合都是華彩段落,照搬也搬不來,必須有新辦法。其實我們主要考慮的是電視劇方式——以人物關系為主。比如電影十幾分鐘來表現顛轎場面和氛圍,而電視劇中這就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要借此表現九兒和余佔鰲征服與被征服的人物關系,雙方能對峙起來,就可以拍(成電視劇)﹔再比如野合,電影裡把九兒夾起來放在高粱地就沒有了,用高粱的高低起伏來交代。電視劇裡我們也是展現征服與被征服,余佔鰲強行,九兒拼死不從,余被踢不干了,九兒反而主動……這裡面有她的叛逆和釋放,所以這場戲不是簡單的兩個人“滾床單”,而是人物性格關系的表現。我覺得這才是電視劇,一點點地去表現人物,現實主義一些,否則你面對經典的小說、電影會不知道怎麼辦。
北青報:編劇趙冬苓提到九兒形象的塑造受到《甄嬛傳》的影響,您怎麼看改編后的九兒形象?
鄭曉龍:關於改編的時候受《甄嬛傳》的影響,這個我不知道。但是總體來講,原來的電影或者是小說,是以余佔鰲為主來敘述故事。但是現在改完以后,主線是在九兒身上,九兒比原來更豐富了。因為電視劇很長,要有更多人物命運來展現九兒,所以更細膩了。
北青報:您怎麼看趙冬苓編劇的改編?有評論認為電視劇版的前半段九兒在單家的故事太像宅斗戲,把一部充滿土地力量的作品改成了家長裡短的宅斗戲,您怎麼看?
鄭曉龍:在家裡發生矛盾就叫宅斗,在宮裡發生矛盾就叫宮斗,在前朝就叫朝斗……戲總要有戲劇矛盾,有戲劇沖突,非要用一個簡單的“斗”來概括,是不是太不應該了……我們要拍在土地上跟人斗,那叫土豆(斗)?我覺得這太可笑了。
關於演員
我確實找不到一個年輕時的姜文
北青報:針對朱亞文的表演,有觀眾認為“演”的痕跡很重,比如故意粗嗓門,面部表情豐富,而並非從骨子裡表現出“匪氣”。
鄭曉龍:我對亞文的表演還是很肯定的。姜文骨子裡也沒匪氣。姜文平時戴個眼鏡,哪有匪氣,他也是演出來的匪氣。姜文不是土匪一樣的人。其實在試戲的時候,我聽別人跟我說亞文演戲有點溫,結果在我面前反倒爆發力很強。在眾多比較當中,我覺得他是最合適的。因為我確實找不到一個年輕時的姜文。
關於爭議
拿電影和電視劇互相比是誤區
北青報:前面播出的幾集裡,有的劇情不太恰當,比如九兒娘死了,她在看到縣長懲罰曹的時候卻笑了起來,再比如與花脖子合計設計她爹與張俊杰,讓人感覺不合常理。當時是怎麼考慮的,在對原作進行擴充劇情方面有沒有一個標准?作為導演對這些劇情當時有沒有異議?
鄭曉龍:當然電視劇要拍很長,總是要有一些新的內容加進去,所以說完全照原來的那個去拍恐怕很難,觀眾也不會滿足。我覺得大家都在拿電影和電視劇互相比,其實這是一個誤區,電視劇是電視劇的創作方式,電影是電影的創作方式,假如我們這個戲拍成三十部電影,你想想光這麼拍行嗎?肯定也是不成的。
文/本報記者 楊文杰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