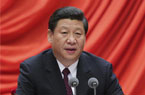溥儀在証人席上宣誓。
近期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是東京審判完整文獻首次在中國面世。整套書80卷、5萬頁、一千萬字,再現了那場耗時兩年多的世紀審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東京審判結束,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用了9天才宣讀完——這只是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宣判,他們當中的七個被判處絞刑。
在東京審判中,最轟動的一幕出現在1946年8月16日,因為一個特殊証人的出場,這一天被稱作“劃時代的日子”。這個人,就是中國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皇帝、廢帝、寓公、傀儡、俘虜、囚犯、普通公民……溥儀的一生扮演過太多的角色,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証人席上時,他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証人。
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直接見証人,溥儀連續出庭八天,創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年庭審單人作証的紀錄。
他為法庭提供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最有力的証人証言,情緒激動時甚至拍案控訴,卻也同時惴惴於自己當年不光彩的角色,隱瞞了部分事實,開脫著自己的罪責。
八天的証人經歷,濃縮了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復雜糾葛。
關鍵証人
1946年5月,初夏,東京市澀谷區杜鵑正盛。紅白掩映之中,滿眼都是破敗景象。戰后的東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毀燒光,遍地焦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的大樓,是斷壁殘垣中完整保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建筑之一。
選擇這棟建筑作為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地有著象征意義。這棟大樓在戰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在戰時是軍部和參謀本部合組的大本營所在地。
日本侵略戰爭發號施令的中心,這時成了戰犯們接受審判的法庭。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
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審判方式,法官必須保持中立,控辯雙方的交鋒是庭審的重頭戲。而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現代法制的兩個基本原則:無罪推定和証據規則。因而從理論上說,在最終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級戰犯們是不能被認為有罪的,而如果他們在控辯雙方的交鋒中佔據了優勢,甚至有被判無罪的可能。
這一點讓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檢察官都很不適應。
中國檢察官倪征燠回憶參加東京審判時曾經寫道:“在審判的第一階段,都是涉及中國受侵略的問題,但中國方面沒有估計到戰犯審判會如此復雜,而滿以為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裡還需要什麼犯罪証據,更沒想到証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
在庭審的最初階段,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証人席的中國証人也無所適從。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到庭作証時,說日本“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被斥為空無實據,幾乎被轟下証人台。事后,秦德純氣憤地說:“這哪裡是我們審判戰犯,還不如說是戰犯審判我們。”
而那些受審的甲級戰犯們,卻在充分利用著法庭給自己提供的“權利”。“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的土肥原賢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發,連法官的提問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電影經典台詞“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現實版。
同樣是“九一八事變”主謀、被稱為“關東軍之膽”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稱自己無罪,甚至叫囂“要與檢察方大戰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個中國証人被帶入法庭,板垣一下變了臉色。
大約在午前11時25分左右,法庭執行官引導著一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証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一縷頭發垂在前額上。與別的証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隻有一名憲兵護送,他身后卻站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在証人席上坐定,這位中國男子用標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紹。
中國的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就這樣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証人席上。 日本最負盛名的報紙《朝日新聞》這樣形容這一天之於東京審判的意義——“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溥儀將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實早已傳揚出去。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遠遠高於往常。曾經定價幾百日元的旁聽券被炒出了數倍的高價,前排的貴賓席平時稀疏冷落,現在卻滿滿當當。
曾經隨侍溥儀15年的“侍衛長”工藤忠百般活動,都沒能在旁聽席上搶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終於搞到一個“某報社的臨時記者的身份証”,卻發現自己隻能被眾多的媒體記者擠在后面……
與那些抱著好奇心態爭睹中國末代皇帝真容的旁聽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諸多甲級戰犯,特別是與溥儀有著直接關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對溥儀的出現大感驚懼。曾經被他們操縱在股掌之中的牽線木偶,現在是他們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証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將他們送上斷頭台。
在溥儀的敘述中,這幾個人的名字不斷出現著。美籍檢察長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儀問道:“你所說的那個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板垣嗎?”
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是。”
有媒體這樣記述板垣的反應:“在法庭聆聽之板垣,聞提渠之名,驟現不安之狀。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觸弄渠之耳機下之電線,當溥儀謂渠運用威脅時,渠之面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嘴之兩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視在場之聽眾后,立即偽作未見,若無其事然。”
証人席上的溥儀,其實內心也不平靜。直到乘飛機從蘇聯到日本的途中,他還在惴惴不安地揣測,自己不是去作証,而是被送回中國受審。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