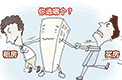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人與妖的爭斗,妖與人的糾葛都是人類文學藝術之林不可或缺的題材。對吸血鬼的描摹與陰曹地府的杜撰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對妖孽的恐懼與憎惡﹔從《聊齋志異》的狐妖與歐洲中世紀陰森古堡的影像中,我們又可以看到人類對妖的敬畏。作為神話傳說與文學藝術中的重要角色,妖已經被人賦予了多種多樣的性格特征與神奇能力,即使這一切都建立在妖的可怕與魔性上,我們還是願意津津樂道於妖魔的奇幻與神秘。似乎隻要談到“妖”,受眾必定為之色變,可愛、純真這些詞語更是與妖這一形象毫無干系。火爆暑期檔的《捉妖記》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妖”的角色進行了重塑,對人與妖的關系進行了重構,將萌妖與人類並置,在奇幻的捉妖過程中為我們展示了人性的善惡與魔性的蛻變。棋類運動中有個術語叫“復盤”,意指將對弈過程重新推演以參透棋局奧妙,我們亦可嘗試對《捉妖記》進行“復盤”,從題材選擇、人物結構、主題闡釋等方面一窺這部打破了國產電影票房紀錄的影片。
以“捉妖”為題材的民間故事與傳說早已成為了中國文學一個亞類型,從“鐘馗捉鬼”到“宋定伯捉鬼”,從“法海降妖”到“倩女幽魂”,在一段時間內,捉妖驅魔甚至成為了國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捉妖”題材的濫觴成為了《捉妖記》故事的重要母本,也為影片奠定了龐大的受眾基礎。
題材的先天優勢並不能保証故事被接受,因此改編與加工是使影片成功的必由之路,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影片對妖精角色的重塑上,更體現在人與妖關系的重構上。在妖精角色的設置上,《捉妖記》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為觀眾奉獻了以胡巴為代表的諸多“萌妖”的形象,這不僅一改觀眾對妖魔的慣有印象,更拓寬了影片的受眾面,暑期檔影片的重要觀眾群體是不同年齡階段的學生,萌妖的出現使他們成為了《捉妖記》以及“胡巴”的擁躉。影片既完成了對妖魔既往印象的修正,又因這次修正拓寬了受眾群落。不得不說,這是一次藝術與市場的充滿智慧的結合。
作為修正后的妖精形象,萌妖的出現便使人與妖的關系不再如以前那樣在處你死我活中,而是相互認知與共同成長。宋天蔭對胡巴、對妖界的認知便經歷了從恐懼、懷疑到信任、攜手的過程。宋天蔭自小被父拋棄,胡巴自幼被母親扔下,兩人的命運是何其相似。這種童年的心理陰影在宋天蔭送胡巴回到大家庭時得以煙消雲散,保護胡巴的同時宋天蔭也完成了自我救贖。
在進行人妖關系重構的同時,本片嘗試著對性別角色關系進行重置,作為男生的宋天蔭被迫生子,身為女生的霍小嵐主動求愛,這與傳統觀念中的性別關系大相徑庭。閆妮所飾演的求子心切的貴婦、湯唯所飾演的利欲熏心的老板、姚晨所飾演的殘忍暴戾的廚師均是極為強勢的角色,分布在他們周遭的則是軟弱的丈夫、苦命的下手這些男性角色,男權社會的法則在這個奇幻的故事中蕩然無存。與此同時,人身上的魔性、妖身上的人性,在捉妖過程中不斷展露,這是影片導演一次新的嘗試,也是從新的視角對人妖關系、性別關系的重新審視。
作為人妖關系中重要的一環,天師群體是影片中角色數量最多的。無論是奉命捉妖、還是為利捉妖,天師們都生存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中:從一文不名的二錢天師,到初有成就的四錢天師,再到傳說中的頂級十錢天師,天師們的等級與他們的法力、裝備、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為了等級的提升,他們忘記是非、拋卻了善惡,盲目且麻木的向上奮斗與攀爬,全然忘記了自己的初衷,這一群體不僅在影片中存在,在人類社會的每個角落都可得見,與其說這是一種諷刺與批判,不如說這是天師群體給我們帶來的警示與隱喻。
天師們在捉妖中逐漸迷失了自我,胡巴卻逐漸觸碰到了成長的意義。它的手在打斗中被割破了,但它的生命卻發生了轉折。從嗜血如命到素食為生,這是魔性的蛻變、人性的生成。這是生命的歷練,又是生命的成長。妖在成長,人也在成長,宋天蔭與胡巴有這共同的生命經歷,雖年少便遭拋棄,卻被人類談之色變的妖精撫養成人,這種生命的成長歷程是獨特的,他拯救胡巴的過程就是他報恩的過程。影片在結尾用時空交錯的方式為我們展現了兩次別離,一個是幼年宋天蔭與父親的別離,一個是胡巴與宋天蔭的別離。這其中有兩對父子——宋天蔭與父親、胡巴與宋天蔭。胡巴由宋天蔭所生所養,放手之時宋天蔭以父親的身份告別了幼年的陰影,這更是他從男孩到男人的一次蛻變與歷練。
在《捉妖記》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在《捉妖記》中,我們看到了兩個年輕生命的成長。在《捉妖記》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善惡與魔性的蛻變。在《捉妖記》中,我們看到了中國電影的成長:繼7月份破54億的單月票房紀錄之后,《捉妖記》又為我們獻上了單片超20億的國產電影票房紀錄。誠意之作總會給人帶來驚喜,希望這種誠意與驚喜繼續伴陪著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2015年夏天,有一部《捉妖記》,與我們共同成長。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博士 天津工業大學傳媒藝術系教師)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