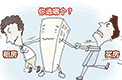三、關於科學知識的閱讀
恩格斯說,一個蘋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蘋果。一個記者、作家隻讀社會科學不讀自然科學,他眼裡的世界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我是學文科的,后來的工作也不是科技領域。但是誤打誤撞,進入了科普寫作。經過“文革”十年浩劫,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后科學的春天來到了,報刊上沉寂了十年后科普文字如雨后春筍。被耽誤了的一代,有的惡補文學知識,搞創作﹔有的惡補科學知識,准備升學或搞科研。我出於好奇,也開始瀏覽一些科學故事。
那時我在《光明日報》當記者,跑科學口和教育口。科技工作者思維活躍,讀書多,常講一些我所不知的,他們學科領域的故事,很吸引人,科學並不枯燥。我也常採訪學校,看到學生讀書很苦,而且不少人對數理化有畏難情緒,心裡煩燥。我發現這原因不在學生,而在我們的教學不得法。科學和教育沒有溝通。小孩子先有形象思維,數理是邏輯思維,很多學生一下子不適應。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我想能不能轉換成思維,把課本裡公式、定理的發現過程、人物故事寫出來,讓學生像讀小說一樣學數理化。我決定嘗試一下。
第一步是找故事。讀所有能看到的科普報刊,按照中學課本裡的內容尋找公式、定理背后的故事。大量剪報,分類剪貼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幾大本。除了剪報又摘卡片。那時還沒有電腦,更沒有百度等搜索,大學一入學的訓練就是手抄卡片。我專門做了一個半人高的卡片櫃,像中藥店的藥櫃。隻讀報刊當然不夠用,又讀科學家傳記,如《伽利略傳》、《居裡夫人傳》、《達爾文傳》等。讀單本書不行,還得宏觀把握科技進步的過程,又讀科學史、工具書,如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自然科學大事年表》之類。有事實和故事仍然不夠,還得惡補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論。現在還留有印象的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德國科學家貝弗裡奇的《科學研究的方法》,俄裔美國著名科學家阿西莫夫的科普系列、中國數學家王梓坤的《科學發現縱橫談》,物理學家方勵之的小冊子《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等。我走的還是經典加普及的路線,讀那些大家的最好的經典普及本。如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淺說》,1964年版,100多頁,才3角7分錢一本。
我寫的第一個故事是數學方面的。我們在初中就學過什麼是“無理數”,這是個抽象概念,怎麼還原成形象?古希臘有個數學家叫畢達哥拉斯,他死后幾個學生在爭論老師的學問。一個叫西帕索斯的說,他發現了一種老師沒有發現的數,比如用等腰三角形的直角邊去除斜邊,就永遠除不盡。別的學生說,不可能,老師沒有說過的就是沒有,你這是對師長的不敬。當時大家正在船上,爭到激動時不能控制情緒。幾個人便把西帕索斯舉起來扔到海裡淹死了。事件過后,他們反復演算,確實有這麼一種數。比如圓周率,小數點后永遠數不完。於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數、循環小數等叫有理數,這個新數叫無理數。這就是我小說裡的第二章《聰明人喜談發現,蠻橫者無理殺人—無理數的發現》。這個故事,教師在課堂上三分鐘就可講完,但學生一生不會忘。我把這故事發在刊物《科學之友》上,大受歡迎,編輯部要求接著寫,結果騎虎難下,每月一期,連載了四年,1985年1月結集出版了《數理化通俗演義》第一冊,1988年三冊全部出齊。有一次汪曾祺先生與我同在一個書店簽名售書,他高興地為這本書題辭:“數理化寫演義堪稱一絕”。這本書先后出了香港版、台灣版、維吾爾文版,重印20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對數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學生和家長歡迎。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科普老前輩葉至善都曾為書作序。這是一部無法歸類的怪書。它的起因,一開始就不是創作小說的文學沖動,也不是科普創作的知識沖動,而是一個記者社會責任的延伸。
科學閱讀的另一個間接的成果是充實了我的散文創作。我們常說,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國,就是說由宏觀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學的眼光看文學,至少寫作時騰挪的空間會更大。比如,我在《大無大有周恩來》一文的結尾處,談到偉人人格的魅力,談到為什麼他們雖已故去多年又讓人覺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對論”的時空觀:“愛因斯坦生生將一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一個哲學結論:當速度等於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再提出一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穹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在《最后一個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說到林則徐被發配到新疆邊服罪,邊工作,測繪耕地,“整整一年,他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萬畝耕地,極大地豐盈了府庫,鞏固了邊防。林則徐真是干了一場‘非分’之舉。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歷史與現實中也常有人干著另一種‘非分’的事,即憑著合法的職位,用國家賦予的權力去貪贓營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貪、分外之私。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遠者莫如人格之分了。確實,‘分’這個界限就是‘人’這個原子的外殼,一旦外殼破而裂變,無論好壞,其力量都特別的大。”這裡借用了物理學上的原子裂變,即原子彈爆炸的原理,來喻人格“裂變”的能量。
在《蔣巷村的共產主義猜想》一文中,寫到這個富裕村的陳列室裡張貼有800年前辛棄疾描寫江南生活美景的詞,又寫到他們現在公共福利的分配方式,就用科學術語來解釋:
基因學有一個術語:基因漂流。自然物種在進化中,總有某種基因會飄落某處與其他基因結合成新的物種。共產主義理論一產生就是一個在歐洲大陸上“游蕩的幽靈”,一個漂流的理論基因、科學基因。160多年后,它漂到中國的江南水鄉,與這裡從800年前漂過來的,辛棄疾詞裡所表達的那個天人合一、老少同樂、物我一體的鄉土基因相結合,成了現在的這個新版本,蔣巷村版(現代中國還有其他板本,如華西村、南街村版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修辭上有一種格叫“拈連”把本是用於描述甲事物的詞匯移來說乙。如“相對論”、“裂變”、“ 基因”都專用的物理、生物詞匯,卻用來說人和事。把科學思維、科學術語用於文學,正是一種跨界大拈連。拈連實際上也是一種比喻,是隱喻。而比喻中甲乙兩物是相距愈遠,性質差別愈大,所產生的比喻效果就愈強烈。
因為閱讀科普作品,同時又採訪科技界,使我有機會參加有關學術活動。1984年8月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一次思維科學討論會,籌備成立思維科學研究會,我有幸參加。這種綜合學科的研討與文學界開會有很大不同。會議人數不多,一共才59人,但名家不少。我過去的偶像如錢學森、吳運鐸、高士其等都出席了,還有80歲的心理學教授胡寄南,美學家李澤厚等。錢學森用一整天的時間做開場報告,后幾天就坐在台下仔細聽。大家自由爭論最前沿的知識,主要是討論思維規律,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不同及聯系。就在這次會上錢學森提出五種思維方式:形象思維、邏輯思維、靈感思維、社會思維和特異思維。耳聽筆記,這是一種近距離的閱讀,讓我的思維方式有了一個大擴張、大轉換。自從增加了科學方面的閱讀,我才知道世界原來有這麼大,思維方式可以有這麼多種。自覺頭腦比原先靈活聰明了許多。后來我與人合作寫了一篇談思維科學的文章,經錢學森先生審定發在《光明日報》上。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