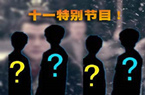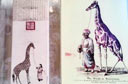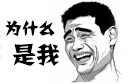“昨天,我的一個朋友被打死了。子彈擊中頭顱。他大概奔跑了十來米,想抓住自己的腦子……你能寫這些嗎?”被採訪者用嘲弄的語氣問阿列克謝耶維奇。他以為,她已經被嚇壞了。
阿列克謝耶維奇還真把這個細節寫進了《鋅皮娃娃兵》,那是一本紀實文學,記錄了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后,10年中所發生的一切——死亡、殘暴、欺騙、苦難、精神失常,還有那些普通家庭失去親人后的悲傷。書名帶有強烈的反諷意味:侵入阿富汗的都是20歲左右的“娃娃兵”,他們帶著夢想離開家鄉,結果卻被放進鋅皮棺材中,又帶了回來。
為了《鋅皮娃娃兵》,阿列克謝耶維奇幾次被告上法庭,她在努力捍衛著一個真相:戰爭就是殺人,士兵就是殺人工具。不是每個人都能面對這個真相,一個失去孩子的蘇聯母親說:“我們不需要你的真實,我們有自己的真實。”
說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寫作是紀實文學,有一定道理,她寫的都是採訪來的東西,通過“剪刀加漿糊”,將別人的回答、日記、書信等拼貼在一起,她不抒情、不拔高,甚至不怎麼交代背景,以維持絕對冰冷、絕對客觀的外殼。此外,她的書中都沒有主人公,她總是將幾十個採訪筆記打亂,並胡亂穿插在一起,讀來猶如一團無序的碎片,因為與日常生活如此同構,所以顯得特別真實。
在相當時期,“真實”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護身符,她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甚至很少在作品中發表議論。這,或者也是一種應對環境的伎倆。
然而,仔細品味,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紀實並非完全客觀,其中隱含著很強的抒情味道——她所截取的,都是最有情感沖擊力的細節,片段與片段也非隨意拼接,而是充分考慮了閱讀者的情緒起伏——一般情況下,她總是先隨意扯一些日常生活的細節﹔緊接著就是最驚悚、最惡心的內容﹔接下來,她會講一個悲傷的情感故事,溫馨卻黑色﹔作為結局,她總能翻出一些當事人似是而非的感悟。
始而誘敵深入,繼而強烈刺激,再則訴諸情感,最后留下苦澀的回味,這一套敘事把戲在俄羅斯現實主義小說中,被大師們玩得爐火純青,而阿列克謝耶維奇竟然在紀實的外包裝下,復活了這一系列大招。
阿列克謝耶維奇最讓人欽佩的地方,在於她的克制力。
阿列克謝耶維奇當然知道自己想說什麼,卻始終不肯站出來,她不動聲色地引誘著讀者,直到他們鑽入圈套,並在情感反復受虐之后,最終自己“悟”出來。她像一個老練而冷靜的獵手,隨時准備擊垮你的心理防線,讓你淚流滿面。
誰不知道戰爭是苦難的呢?誰不知道苦難兩字的重量呢?但阿列克謝耶維奇永遠能把苦難說得與眾不同,以使你明白:它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詞,真正的苦難是沒有旁觀者的,面對它時,我們無處可逃。
其實,又有多少虛構文學的作家,能像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樣,把苦難說得這樣驚心動魄?
在《戰爭中沒有女性》中,一個女兵回憶道:“我從前線回來時才21歲,已經是個白毛女了。我一隻耳朵被震聾了。每當半夜裡聽到附近礦井開採爆破的聲音,我就會從床上爬起來發瘋地往外跑……”
這本書寫了衛國戰爭中那些被忽略的女戰士們,書中這樣提到了她們所受的傷害,一個當年的女兵幾十年后一直不敢進肉鋪,不敢看肉,特別是雞肉,因為雞肉讓她聯想到人肉,每次戰斗結束,它們散落在戰場的各個角落。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克制力還體現在她的文字中,她很少寫痛徹心扉,專寫苦難的漫長回聲,寫苦難對心靈的扭曲,以及我們想忘掉苦難時,裝出的那些從容。
在《最后的見証人》中,阿列克謝耶維奇寫了100個人回憶童年時所見到的戰爭,她不懷好意地寫道:“主人公不是政治家、不是士兵、不是哲學家,他們是兒童——不偏不倚的見証人。”可這些見証人告訴我們的又是什麼?
“當我目睹了在他們機槍的掃射下,我的爺爺和奶奶中彈而死﹔他們用槍托猛擊我媽媽的頭部,她黑色的頭發變成了紅色,眼看著她死去時,我打死了這個德國人。因為我搶先開了槍,他的槍掉在了地上。不,我從來就不曾是個孩子。我不記得自己是個孩子……”
在《鋅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謝耶維奇記錄了一個蘇軍士兵遺孀的心聲:“我24歲當了寡婦。頭幾個月,任何男人來找我,我立刻就可以嫁給他。我瘋了!我不知道怎麼才能自救。”悲傷讓她無法重建自己的生活,而當她以為終於可以平靜時,局面突然逆轉。“當我第一次從電視上聽說阿富汗是我們的恥辱時,我把屏幕砸碎了。那天,我第二次埋葬了我的丈夫……”
不知道阿列克謝耶維奇是怎樣採訪到這些故事的,也不知道她因此遭遇過多少拒絕、恐嚇和羞辱,她深入了受害者們的心靈,抓住他們稍縱即逝的瞬間精彩,她耐心地將這些編織進自己的抒情圈套中,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她絕不會為了圈套的完美,匆匆跳出來裝點一番,或者是因為她手中的猛料實在太多了,多到讓她不屑於去“拔高”。
我們曾經以為,紀實文學是出不了大師的,因為它不永恆,既不能延續小說智慧,也無法成為成績豐厚的小說文化遺產,但,阿列克謝耶維奇卻展現了另一種可能——即使是在我們曾經的報告文學繁榮時代,我們也很少注意到這種可能——紀實文學未必要指點江山,未必要汪洋恣肆,未必要“有用”於時代,它也可以回到人的層面,成為現代社會中愛、悲憫、真誠等等情懷的培育所,它是所有人的文字共和國,我們走入其中,收獲了更豐富的共情能力,紀實文學與經典文學又有什麼分別?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注定都是沒用的,所以本文開頭提到的故事有一個搞笑的結尾:7年后,阿列克謝耶維奇又見到了曾經的採訪對象,此時他已經是個大富翁,他對阿列克謝耶維奇說:“你那些書有什麼用?那些書太可怕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